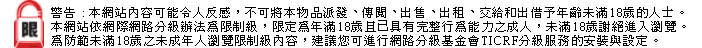6之大結局裸殺
之大結局__裸殺
——臨刑女罪奴林青青與菲臘主人
每一天每一天深夜,被捆緊在地下室中的我都盼望著精神的徹底崩潰,或者身體的極度痛楚,能夠使我產生一點點迴光返照式的幻覺,或者昏迷。可是我從未得到這樣的幸運。
我平舉在體側的手臂被粗大的繩索纏繞著繫緊在牆上,雙腳只有前兩個腳趾能夠觸碰到地面。這樣地貼著牆我已經站立了四個晝夜,四個晝夜中疼痛使我幾乎沒有合上過眼睛。
無論哪個女人的兩隻乳房像我這樣被刀刃一小片一小片地割下去,直到割成胸脯上的兩個深坑,她也會像我這樣難以入睡的。而且每天結束的時候小許從不會忘記給這兩個破破爛爛的大傷口上擦進許多的鹽。
在這樣的夜中我不得不大睜眼睛凝視著暗淡的屋角,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回憶我這四年的性奴生活。
作為一個年輕的女人,我竟然能夠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地生活了整整四年,赤露在市鎮,鄉場的眾目睽睽之下,每一天,每一個鐘點,從未得到過哪怕是一縷布條的遮掩。
毫無疑問,主人也將讓我就這樣赤露著死去,裸身上僅有的是我這四年中沒有片刻解脫過的鎖鏈。
除了叢林深處和一兩個小海島上的原住民婦女,我想這肯定會是個難得的經歷吧,就是她們也不會終日戴著鐵鏈,也不會在陰唇上紮著一個小鈴鐺的。
我已經完全不能記起繫上一條美麗的裙子會給女人帶來的驕矜心情和春天一樣的浮華,其實我已經連穿著鞋走路是什麼觸覺都不知道了。
我會問一問自己,不戴鐵製刑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會輕快一些?
對於一個曾經在前半生中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挑選,收藏漂亮的花布和絲綢的城市女人來說,這真是一個大諷刺。
在親身體驗過這些之前,不一定能想到赤裸地生活還會有許多其他意想不到的麻煩和難堪,它並不總是那麼誘惑男人。
在女人每個月都會碰到的那個週期裏,有三到四天經血一直在淋淋漓漓地流淌出來,不是經常允許我擦掉的,就算讓我擦也不一定能找到東西。
這不是在自己家:洗手池邊是我的毛巾,茶几下還有面巾紙,沒有許可主人房裏的任何東西女奴根本碰都不能碰。許多這樣的小事會變得意想不到地折磨人,我都沒有怎麼說。比方說,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給我盛飯用的那個破瓷碗,想一想,從那以後我是怎麼吃的飯。
經血流遍了我的腿和腳,走一步,就在地上留下一個血印子。憋急了的兵碰到這種時候會幹出什麼來真很難說。
我在分娩的第三天就被打起來掃院子洗地板去了,而女人的下身要到生產後一個月才能完全乾淨,那些開始紅,後來白的東西也就那麼地流著,乾結著。
四年當中我在不停地接受著男人們,用我女人身上的所有洞穴。
不僅如此,那還經常是在公開的,熱鬧的場所,比方說:臘真鎮擠滿觀眾的軍營門外,一遍一遍地當眾進行我們的性交表演。
如果平均一天被奸二十次的話,可以算一算四年來我有過多少次的性關係。
既然這幾個夜是那麼的難熬,那麼的長,我自己為了打發時間是計算過的。至於這四年中觀賞過我赤裸身體的人,忘了他們吧,不算也罷。
每一天都挨打,一早一晚的各十下鞭笞是從不會忘記的。
還有晚上的那一回,用粗木棒上百次地摩擦自己的陰道。至於其他那些更特別的,反正我都已經說過了。
噢,不過我想到了這裏有一點例外:就是我緊緊團起手足,低頭躬腰整月整月蹲在水泥坑洞中的那些日子,那倒不是每天都要打,都要捅自己的。那些天也見不到幾個男人。把我拽出來塞進去的太麻煩,有時阿昌會記得叫兩個小保鏢做,有時他們就放過了我。
還有在金礦的那一年也好一些,那到後來就只是克力的玩笑了。
連我自己都吃驚地看到了我身上的潛在能力,在經過了驕縱地享受寵愛的二十四年之後,我學會了許多更基本的事,那是一個女人用她一無所有的身體也能做好的:
比方說背水,或者如何取悅許多的男人,孟昆已經使我懂得了我甚至能夠憑藉著這些生活下去。不過我想再也用不著,這一回大概是真的了。
還在開始割我的第一天,一個弟兄就當著我的面把陪伴了我四年的那根小木棒改造成一個殘忍的玩具。
具體地,是用鉗子夾緊了縫衣針,靠鐵錘幫助向後傾斜著釘進木棒中去,然後夾斷針尾露出的太長的部分。
許多的細鋼針在木棒的前半部圍成幾個圓圈,這樣這個東西看起來像是一個帶著一些倒刺的狼牙棒。
主人要這個玩具在我生命的最後十天中更緊密地陪著我。
它幾乎像是一件活物,當它被插進我的陰道口後就憑藉著那些密密的鋼製小腳自動地爬向深處,從不會後退。因為我的肌肉在疼痛中收縮,我的腿會忍不住地抽搐,我下半身的任何動作都是對它的幫助。
它現在已經頂進了我陰道的最頂端,在緊壓著我子宮頸的地方,柔和地痛著。
我用空著的左手摩挲著它露在我體外的握把,一些粘液和著血流出來。
我的主人已經殺過十幾個也許幾十個年輕女人了,他決不會幹出用尖木棒直接刺穿我的陰道這樣愚蠢的事。
重要的是不要弄破臟器造成大出血,一個飽受摧殘的女人就仍然可以活著而且痛下去。
從今天開始,接下去的四天裏會開始折磨我的兩隻腳,也許還加上我的雙手,主人已經說過我在死之前會親眼看到自己的身體上少了許多東西。
他們大概還會再讓我活上四到五天,我真希望能快一點。
我現在還能在這裏輕鬆地寫下我緩慢的死亡過程是因為今天早上當太陽光線終於射進這間地下刑訊室的時候腓臘走進來站在我身前。我已經顫抖了整個晚上,不知道前言不搭後語地對他說了些什麼,大概總是哀求他放開我讓我躺下來吧。
他盯著我看了一陣,似乎真的露出些憐憫的樣子。
「我們都喜歡看妳給你老公寫的那些東西,我想妳老公也會喜歡的。我把妳解開,妳答應再寫上最後一段。今天晚上我們就要開始煮熟妳的手,那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他真是瘋了,我盡可能地搖頭。呻吟著說:「不,哎呦,不啊——」
「隨便妳,妳可以這麼靠牆站著等到晚上。不過要是妳同意,我會讓黃醫生給妳打止痛針,至少整個白天妳會覺得好過多了。後面還有四五天要忍呢。」
他無所謂地說。他知道我最後只能答應。
打過杜冷丁以後確實不那麼疼了,我對著桌子發呆,不知道還有什麼可寫。腓臘和氣地啟發我,他真是很少這樣好心。
「小母狗,別去管妳就要死的事。多想想那些美麗的,婉約的,純情的——就算妳不想多說那個給老公戴上了綠帽子的小雜種,總得彙報一下妳下面那個洞洞的狀況吧,她是怎麼變成現在這麼付怪樣子的?妳老公肯定會在乎的,那是他的寶貝東西嘛。寫著寫著妳就會感傷起來,妳就會想到妳其實已經連胸都沒有了!哈哈哈!」他說。
好吧,隨他的便吧。
去年年初巴莫把我從金礦裡弄回來後沒有人費心給我解釋,我也沈默著,女奴從不提問。
唯一可以高興的是讓我見到了我的女兒,她已經兩歲了,不認識我,可是也沒被我身上的血跡和鏈條嚇住,她真是很膽大。
她的保姆告訴她我是一種會站起來走路的狗狗。
一切恢復了原樣。噢,還有一個需要恢復原樣的是我的肚子。
在M國雨季的一個早晨,我在細雨中扭擺著寬寬的腰和臀艱難地走上山坡,拳起的腳趾頭在細膩的紅泥漿中滑來滑去。剛剛在下面營地裏陪士兵們做了整整一夜,腰腹酸痛得只想蹲到地下去。
別墅大門口懶洋洋地靠著幾個主人的警衛,他們可有可無地注視著我越走越近。
「嗨,小婊子,吃了嗎?」有個弟兄對我打了個招呼。
我恭恭敬敬地停住,「女奴隸還沒有,叔叔。」
「先來吃點叔叔的水吧。妳那麼賤,肯定饞了一個晚上了。」
我向下跪到泥水裏,熟練地解開褲帶把他的褲子褪到膝蓋上,把頭伸進他的胯下晃動起來。
被我含在嘴中的這個保鏢抱著肘低頭向下看,對於他和他的同伴來說玩弄我早就像上個廁所一樣平淡了。
我十分敬業地由緩而疾,讓長頭髮飄散開來,並且開始發出尖叫聲。同時我還得平舉雙手為男人提著褲子。而上面的警衛卻彎腰拽緊了我的頭髮,把我的整個身體突然提了起來。他的兇惡的臉正對著我的眼睛。
「妳這條母狗,妳真有那麼餓嗎?」男人鬆開一隻手象熊掌一樣重重地抽在我的臉頰上,反過來第二下,同時放開了我。
我被打得向一邊側摔出去,另一個人趁便踢了我一腳。
第一個人因為生殖器還在胯間挺立著,火氣旺盛,他從攤在地上的褲管中拔出腳來,光著下身上前兩步拽起我的身體,按照他們民族傳統的搏擊方法抬起膝蓋猛撞我的腹部,第三下重重地頂在我的左乳上,鈴鐺一聲脆響。然後他鬆開手讓我縮做一團滑落到地下乾嘔著。
這幾下更增加了他的男性氣概,他跟著壓上來進入我的體內。他大聲哼哼著,接著大量的血就從我的陰道中激流出來。
我捂著劇烈疼痛的肚子慢慢地撐起半個身體,沾了滿身的泥漿,在我兩腿之間的血泊中浸著一個帶小胳膊小腿的肉團。
「叫黃先生來!」我聽到有人說。
那以後誰都知道我就是在等死。我越來越倦,陰道和肛門也越來越鬆。
在我獨自待著的時候尿液會不知不覺地順著我的腿側流下去,直到把腳全浸濕了我自己才發覺。我想接下去我的後面也會發生同樣的事。可以想到在這樣的情形下有興趣玩弄我的人越來越少,至多是讓我用嘴給他們吮一吮。
偶而大家來了興致就更壞,他們會讓我分開腿猛揍我的陰戶,一直把我打腫起來才開始做。就像後來阿昌用「木頭老公」對付我的那次一樣。
結果我一個人整天整天地跪在保鑣的屋子角落裏發呆。沒人操我的結果竟然是,我自己陷入了空虛和憂鬱之中,以我現在的處境,除了讓人幹,我還活著幹什麼呢?
我記得我就這麼呆滯地注視著黃黃的尿水又淌了下去,然後就想我的確是該被主人帶出去剝皮了。
沒什麼人還來碰我,大家打我的次數也少多了。
值得提到的就是兩次。
先是阿昌因為一件我已經想不起來的事生氣,他想法找了一個中間空的木頭框子離開地面架起來,讓我臉朝下趴在上面,手腳緊緊地捆在框邊的四個角上。我兩乳上掛著的銅鈴鐺在框中間向地面垂下,他再點起兩支粗大的香燭伸進銅鈴裏烤著。
我同樣俯伏朝下的臉緊盯著這對銅鈴慢慢地被燒成了暗紅色,熱力一直透入插在肉中的那兩根鋼釘,我的乳像是要炸開似的發燒。
因為緊貼這兩塊大烙鐵最近的就是我的一對乳頭,所以到這一天結束的時候她們已經變成了薄薄的一小層黑硬的焦痂了。
把我解下來以後沒讓我休息,而是叫我對著牆站直身子,用細麻繩拴住鈴鐺的掛環繫在牆面上。我的手還是被縛在背後。
這樣當阿昌帶著他們要走的時侯我真被嚇得魂不付體了,我還能靠我這雙腳在地下站多久呢?
他們還是大笑著走了,我在裏面獨自站到第二天上午。有很多很多次,我實在撐不住了,下了決心要拉出這對銅掛件來馬上把自己在地下放平。可是稍微試了試那樣可怕的劇痛又讓我想要再堅持一會兒。再堅持一會吧,我用額頭頂著牆壁可憐地左右扭動著身體,拚命想把自己安排得好過一些。
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我才最後拉裂了我自己的乳房。我不能置信地盯著留在牆面上搖晃的銅鈴,那兩根在我的乳中深藏了兩年半的鋼釘和它的倒刺上連筋帶肉地纏繞著一長串我的乳腺和乳管,往下滴著血,然後我就昏倒在地上,終於能夠躺下了。
這是個開頭,大家開始系統地破壞我的身體,下一次就是毀掉我的生殖器了。
那一次我的主人是很認真的,把我仰天捆緊後墊高我的臀,把一個裝著硫酸的玻璃瓶象輸液似的吊起在我的肚子上面,調好了位置讓裏面的酸液一滴一滴地正好落在我的陰埠上。積多了以後它們會沿著陰唇順勢向下流,一邊滲入到大陰唇的底下去。
我叫得跳得是那麼的利害,以至於阿昌他們要停下一會把我的腰和腿捆得更緊些。
攝像頭對著我的大腿根,人們把二十五寸的監視器放在架子上給我推過來,讓我能夠看到自己整個柔和的陰戶是怎樣冒著青煙,一點一點變成一堆黑褐色的破爛。
黃醫生這才帶著他的手術刀來到下面。就讓我躺在那張不銹鋼的臺子上,沒有費事給我麻醉藥便用刀刃削掉了我那片地方所有壞死的皮膚和肉,最後把一大一小兩個塗了藥膏的紗布卷塞滿我的陰道和尿道,這是為了在接下去要做的事情中別讓這兩個管道粘起來。以後在整個的癒合過程中他一直負責任地這樣做,一天一換,要不瘢痕一收縮起來恐怕就沒有他們要的洞洞了。
黃醫生拍拍手直起腰來,手術刀割完了以後我的血流得像小河一樣。他弄來了一大團紗布棉花,打算給我捂在上面,不過阿昌把他推開了。
兩個保鏢正在旁邊的火爐子上烤著一把園丁用的小花鏟,鐵鏟面烤得通紅透亮了以後從我的小肚子往下一路按下去,把血全給止住了— —那一天那整間屋子裏瀰漫著的,又濃重又嗆人的油煙,怎麼會那麼難聞啊!
第三個陪了我那麼久的鈴鐺扔在地上,我身上再沒有掛它的地方了。
到了十二月份主人告訴我我該死了,然後便逼著我寫這四年的經過。
寫第一篇時我還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動,後來就平靜多了。斷斷續續地一直寫到二月份。
我的主人大概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變得這麼有趣,碰到我不願意寫了或者是寫不下去的時候他就動手打。我主人的經歷使他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打出來的,連寫字也是一樣,他早上交給我二十張稿紙,要是到了晚上我還沒寫完就讓我伸出腳來,用「木頭老公」猛砸我的腳趾頭。
然後他去讀那些剛寫完的,覺得不夠淫蕩就再砸第二遍。要就叫弟兄們把我輪姦上一整夜,讓我去「體會體會感覺」。
我一次次地昏死過去,又一次一次醒轉過來,十個腳趾血肉模糊,碎骨頭尖都從趾關節上戳出來了,疼得我臉孔煞白。
我的主人卻笑咪咪地說:「阿青,妳就像是一千個阿拉伯晚上的那個公主,全靠給她老公講故事活著。」
他說的大概是「一千零一夜」,山魯佐德也不是公主,不過能聯想起阿拉伯的「麻醉製劑商人」就已經很難得了,我的主人的確與眾不同。
故事總要講完的。
二月底寫完了金礦之後我一直扭曲著蹲在洞裏,連弟兄們都沒有再來找過我,主人早就說過,我現在並不是靠屄活著。
四天前的晚上把我從裏面拉出來,直接捆到了隔壁的拷問室裏。
他們告訴了我要用十天的時間來殺我,告訴了我每一天要做些什麼,緊跟著就在我的乳房上割開了第一條刀口。
他們甚至都不肯答應再讓我回到地面上去看一看,讓我的光腳掌踩一踩濕漉漉的青草地,呼吸一兩口晚上的風。
「等我們用木頭樁子插著屁眼把妳舉起來的時候妳就會呼吸到新鮮的風了。」他們保證說。
在我早已沒有嫩膚、全是疤痕的乳房根上沿著邊割開一道弧線,然後與它垂直著往乳尖方向切出另一道裂縫,用小巧的尖嘴鉗夾住肉皮呈三角形的開口向上拉起來,同時把刀刃伸進傷口下面劃掉那些礙事的筋膜和脂肪。在皮瓣翻起一兩個平方寸後把刀換到前面來割掉它。
用冷水把血沖掉,一直把下面裸露出的脂肪洗成軟白的棉絮狀的東西。再接下去劃裂後面的皮,再撕起來。
他們做的很慢,不理睬我是如何的哭叫哀求。要是我疼得昏厥過去還要費事把我弄醒。
這樣一天下來只是剝掉了我雙乳的表皮。少許把大把的鹽倒在自己的手掌上整個地搓揉了她們一遍,把我一個人留在牆上,讓我盯著自己胸前這兩個赤紅色的大肉團好好地感受一個晚上。
下一天看著閃光的刀片貼上我浸透了黃水的嫩肉我就想開始尖叫了,只是想想而已,我叫出的不是聲音,是帶血絲的胃液。
刀切在去掉了皮的裸肉上真是尖利得可怕,還是那樣也劃開一個三角,然後把一條不成形狀的肥肉撕扯下來。
女人那麼鼓鼓的乳房外層包裹著的全是一條一條的肥肉,慢慢地又割了一整天才露出下面成串的連著管路的腺組織,看著讓人噁心,這些東西他們都用尖嘴鉗,有時是用手抓住往外拽掉。一下一下都像是在拽著我的心。
到昨天早上我的胸只剩下了乾乾淨淨兩大片深紅色的鮮肉,我學過一點生理學,知道這是我的胸大肌的表面。還有幾條連到我身體內部的肌腱被亂七八糟地切出了橫斷面,這本來是我的身體牽起我的乳房用的。
人被割掉胸大肌並不會死去,所以昨天一天他們就繼續往下割。要是不小心弄破了大血管就用燒紅的烙鐵按一下止住血。割掉一片看看我的反應,抹上些鹽,再割下一片。
我嘗到的痛沒有辦法說得出來,現在一去想我就在發抖。每割下一層我都像衝過一個澡那樣出一身透汗,他們不停地給我喝水。
最後我得感謝我的主人,他遵守了他的諾言,在這件事情開始以前他托了好幾層關係把我的小小的女兒送回了國內,為了讓我放心還請那邊拍了照片通過網路傳過來。我就不說在照片上是誰抱著她了。
在這之後,她的小媽媽隨便遇到什麼都沒有關係了。
天暗下來了,我疲倦地放下筆。我對腓臘說:時間到了,叫他們再來吧。
現在是腓臘
我們是這樣解決小婊子的手和腳的。在她被那麼多男人幹過之後,也許可以叫她老婊子了。
把她的兩腳併攏捆緊,以男人的眼光看這對赤腳真不像是一個有趣的女人的一部分,她們乾枯而且強悍,在突兀的骨節上緊裹著堅硬斑駁的厚皮,看起來顯得很髒。
更奇怪的是她的那些腳趾頭,有的朝這邊,有的扭向另一邊,有的勾在腳掌上伸不直。我恐怕可以把她們形容為雌鷹的腳爪。
如果她們再稍微地柔弱些的話我也許會建議老闆找個砂鍋來把她們活活地放在裏面加點紅棗當歸煲到爛熟。
現在決定採用更猛烈的辦法,小許在旁邊燒了一大鍋水,使它保持著冒泡沸騰的樣子。
巴莫從裏面舀出水來澆到小婊子的這對後腳爪上,因為滾水四處流開去,所以連著澆了很長一陣才把她的爪子燙得紅腫著肥胖起來,表面看起來也乾淨柔嫩多了。
用鋼絲刷子試了試,雖然小婊子疼得「哇呀哇呀」地亂叫,被撕裂的表皮還是沒有被容易地刷下來,只好叫巴莫再往上淋滾水。
原則是:一直燙到表層的皮肉容易地剝落下來為止。
我們試著叫這個不怎麼走運的女人在空隙裏對著答錄機再說點什麼,不過她不太配合,大致上是這樣:「嗚嗚,疼啊疼啊,——腓臘呀昌叔,媽呀——女兒寶寶呀——朝我開一槍呀,打死我啊——不要啦——啊嗚——嗚」等等,沒什麼大意思。所以只好由我把接下來的事寫完,總得給警察們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按照我的經驗,警察不喜歡有頭無尾,他們總想知道壞蛋最後把屍體藏到哪裡去了。
為了不把這件事拖得太久,同時就開始用滾水燙她的手,泡脹起來的爛肉也用刷子一層一層地刷掉。
有時候也順便往她的身上潑一勺開水,一下子就使小婊子像是要跳起來的樣子。就是說,在她的手腳被刺激過度變得不太敏感的時候調節一下氣氛。當然大多數時候我們會好心地讓她休息一陣,有時還需要給她注射強心劑來使她保持清醒。
下一天起要給她餵點參湯來維持她的體力了。我們有點擔心她沒有經過完全的體驗就被活活痛死,決定提前一點給她享受最後的肛門之戀。
這樣在她的手腳骨骼上還粘附著成條的暗紅色肉塊時就把她拖到大門外邊,這裏已經準備好了一根手腕粗的長木棍,挖好了一個深坑。
雖然女人的肛門並不太緊,但對於這樣的木棍還是太窄了。要先用匕首插進去割斷她口子上收緊的括約肌,這是主要的障礙,再往裏人類的肚腸就有很好的伸縮性了。
反綁上手,抬起木棍來小心地往她的屁股眼裏捅進去,在上面真的塗了不少汽車用的黃油。
在插進四五十釐米後把這個大肉串搬到土坑邊,小心謹慎地把它豎起來埋進去,這一道花了我們很多力氣。
一直閉著眼睛軟軟地聽任我們擺弄的大姑娘這下真正覺得難受起來了。她把兩條細細的長腿向四下裏亂蹬,從嘴裏噗噗地往外吐氣,吹出了成串大大小小的泡泡。她越動,插在木棍上的身體就往下沈落得越深。
另外一個免費奉送的優惠是隨著她掙扎,鑽進她陰道裏的狼牙棒也會活動起來,希望它在裏面契而不捨的努力會讓女人得到反諷的快慰。
老闆不喜歡她還能閉上眼睛,於是阿昌親自站到一張椅子上捏起她的上眼皮用刀片劃開扔掉。血會流下來,會使她的視野變紅,可是稀薄的液體是不能完全遮黑光線的。這樣她就得一直睜大眼睛看著自己既沒有乳房,也沒有手腳的光禿禿的軀體奇特地坐在半空中。當然我可以想像,她看到的這一切都沈浸在一種粉紅色的氛圍裏。
除了喘著氣悲鳴之外,她對湊到她臉前的阿昌說了她這一生中最後的一句話:「謝、謝謝你們,讓、讓我死。」
我們的確把她教成一個很乖的女孩了,不是嗎?
她恐怕還是低估了我們的耐心,因為她才在木樁上苦熬到下午就被我們砍斷木頭放了下來,躺在草地上接受阿黃給她輸液。她瞪大了沒有眼瞼的眼睛盯著我,血紅血紅蠻嚇人的。
我找了把小刀走過去,她勉力動了動嘴唇,也許還想試著最後一次要求點什麼,等我微笑著動手慢慢地割她的耳朵時她終於忍住了。
這樣我再順帶著費點事剜掉了她的鼻子。這張臉現在亂糟糟的像是一個屠宰場,正好配得上一個沒有乳房也沒有陰唇的女人。
在我後面小許他們忙著把蘸了煤油的小布條用按釘釘在她的身上,左一條右一條地點起火來,這些只能算是飯間的開胃酒。
她在她希望得到的潮濕的草地上躺過了這一夜。在早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再一次把她穿到木樁上豎直,估計這會是她的最後一天了。
把煤油澆在她陰道口外留出的木柄上點起火來,火苗在那塊地方舔來舔去地燒了一會兒,便不聲不響地順著可燃的木質向深處推進。
這種在後花園裏小燒烤的樂趣,我恐怕我們的姑娘在這四年中已經是很熟悉了,那就再把碎布塞進她的嘴裏也點上火,在這裏總算用完了最後剩下的一點燃油。
明顯地她還是覺得痛的,這個殘缺不全的女人體現在發出的聲音和她稀奇古怪的形體動作的確已經無法形容,勉強說說,也許就像是被四五十條漢子幹得奄奄一息的大姑娘又被弄到了性高潮。
老闆答應過的,給她已經露著骨頭的兩隻腳腕各拴上一塊大石頭。
戴濤,8號晚上告訴你這個網站的電話是我叫人掛的!我知道你一定會來這上面,來看看你的小妻子是怎麼苦苦熬過這四年當中的每一天。
DOWN 下去一遍一遍仔細地看吧,好好想想這四年裏你的女人是怎樣精赤條條地拖著鐵鏈爬過來爬過去,被我們扁得大聲尖叫,我踢她就像踢我的狗一樣。
她現在還沒有死,說不定還能活到今天晚上呢,我們都認為很有希望看到木樁最後從她的喉嚨口裏鑽出來。
你選擇做我們的敵人一定會痛悔終生!
——————–
製作工具:小說下載閱讀器 http://www.mybook6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