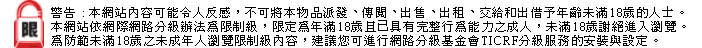隔壁漂亮的年輕老師雨瓊
隔壁住著一對年輕夫妻,幾個月前剛結的婚。那男的姓張搞銷售,常出差。女的倒是常在樓道,電梯裡遇見。她見面只對我談淡一笑。沒跟我說過話。她端莊秀氣,紅唇飽滿,甜美中帶點兒性感;一雙高聳的乳房顯示出特有的少婦的韻味。她叫李雨瓊。是個中學語文老師。
她呀,一定是她班上所有小男生的春夢對象。
有一天,電梯裡站在她身後,看著她擡高雙手擺弄頭髮的樣子,美極了。真想伸出雙手從她的腋下滑過,摟住她那對可愛的乳房。勃起的弟弟差點頂到她高翹的臀部。以至於下一次見到她,我先不好意思起來了。真羨慕她老公小張好福氣。大千世界,有些事,不服不行啊。
那天,我正在午睡,被隔壁一陣陣響亮音樂聲吵醒。
今天是怎麼了?平常他們小二口總是安安靜靜的呀?
忍了一會兒後。實在忍不住了,便去敲門。「小李老師,你在家嗎?音樂聲能輕一點嗎?」
沒有回應,但音樂聲依舊很響。
再敲,「小李老師,音樂聲能輕一點嗎?」還是沒有回應。
「開門,要不我報警了!!」我有點生氣,脫口說了這麼一句。
「噶∼」門突然開了。見一六十幾歲猥猥瑣瑣老頭站在門後,滿嘴酒氣。
「對不起,小李老師在家啊嗎?」我感到有點奇怪。
「在,在裡面∼」他示意我進去。
以前從沒進過小李老師的家。我沒多想,帶著好奇,跟著他走進客廳。
眼前的情景頓時讓我驚呆了。
客廳中央的的一張椅子上,坐著一白嫩的少婦,臉色紅潤,蓬鬆的秀髮淩亂的散在胸前,她的雙手被綁在後面,嘴上還被貼了張膠帶紙。她看了我一眼,先有點激動,然後又羞澀把頭低了下去。顯然,她不想讓我看到她這個樣子。
我的目光來到她的胸前,白襯衣鬆開了,露出小鵝黃的胸罩,胸罩左側的帶子已被扯斷。由於乳房豐滿,左罩杯還沒完全落下。但大半個乳房還是露了出來,很白。左奶頭清晰可見。這個就是小李老師,她在流氓面前毫無招架之力,只能發出叫床式的呻吟。活脫脫一個等待著被操的小少婦。
「你想幹什麼?」我轉身一把抓住那老頭的領口。
「別動,再動我殺了你!」
我感到一把冰涼的刀子在我的脖子上。
慢慢轉過頭來,拿刀的是個小年輕,個子不小,但最多18,19歲。嘴上剛長出一點細細的唇毛。啊,我應該想到,這裡不止老頭一個人。
「別亂來,有話好說!」我高舉雙手,真的有點怕。
小李老師對我此刻的熊樣真的很失望。當然,這是她以後告訴我的。
「我偷錢,他竊色,誰讓你來多管閒事。」
老頭推開我的手,回到桌前坐下,繼續喝他的酒。
奧,還是好酒拉、菲呢呢。
「算我多事好嗎?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我走了,你們繼續。」我裝作要走。
「唔。。。」小李老師在那裡不停地搖頭,她盯著我,目光裡帶著哀求。
我平靜地看著她,向她點了點頭。意思是我不會丟下她不管的。
尖嘴大叔自個喝著拉菲,已經有點兒迷糊了。
「這位大哥,不滿你說,今兒我倆頭一次動,動手,只弄了二百五。你說晦氣不。」
「你以為城裡人都有錢啊,現在的年輕人都是月光族,二百五也不錯啦,你們見好就收,在警察來之前,走人吧。」
我又轉過頭去,面對小李老師,「你呢,也不要報警,好嗎?咱們和平解決。」
小李老師雖說不出話,只是在哪兒不停地點頭。
「我倒還好說,嘗到了這好酒,可這柱子還是個童子軍呢,你讓他開個葷行不。」
「行嗎?」我問小李老師。
可憐的雨瓊,不停地搖頭。
「她不同意,那就是強姦!!」我大聲說道。
「只有姦了她,她才不會報警。」尖嘴大叔道。
「是啊,我幹了她,看她還敢報警。」柱子把手中的刀在空中揮了一下。
「你不要命啦?強姦是要罪加一等的。」我想嚇他們一嚇。
尖嘴大叔走到我身邊道,「你這位大哥,江湖上都這麼說,只有姦了她,她才就不會報警。」
「是的,江湖上,是這麼有一說。但為什麼還是有很多的強姦案受害者最後都報警了。強姦犯也都被抓了。」我道。
「為什麼?」他們有點緊張了。
「有的強姦案受害者沒報警,是因為她們最後被強姦者從精神上、肉體上徹底地征服了。懂嗎?當然太複雜你們也聽不懂,只有被乾爽了,才不會報警。」
「哈,不就是把她幹爽了嗎?誰不會!」尖嘴大叔喊道。
「說得容易,瞧你那令人噁心的瘦猴樣,又喝了這麼多的酒,到時候只怕半硬不硬,插不插的進都難說,你有那本錢嗎?把她幹爽,在做夢吧。」
「那我們柱子行,才18歲,挺起來槍老硬老硬的,玩死她。」
「柱子他是有本錢,但沒本事。他有過性愛經驗嗎?沒有吧?毛手毛腳的楞頭青,老硬老硬的弟弟我信,能插進去我信,不把她弄疼才怪呢?進去以後,他HOLD住嗎?面對這麼年輕美妙的少婦,三下兩下一定一瀉千裡。」
「你、、、」柱子惱羞成怒,擡起手來打了我一下。
「慢,這位大哥說的有理。」尖嘴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你說咋個玩法呢?」
「第一,你要尊重她,讓她知道你要幹什麼,如何幹,她雖不會同意,但讓她心裡有個底。能減少她的緊張和不安。」
我一邊說,一邊把她鬆開的乳罩向上提了提,蓋住了幾乎裸露的左乳頭。我沒有看她,但能感受到她感激的眼神。
第二,別讓她覺得噁心,你幹前得刷個牙巴,洗個澡吧,你該帶個套吧?」
「我這就去洗∼」柱子把自己脫得只剩一條短褲,刀也被他丟在一邊。
「第三呢,要有耐心,你得不停的與她說些情話,挑起她的情慾,減少她的負罪感。
第四,你要有技巧,不停地換花樣並不見得好。到不如一些簡單,有節奏的,重複的刺激會更有效,弄得好的話,她呢,會對下一個刺激有所期待。」
她認真的聽著。看到我在看她,她轉過臉去,不敢看我。
「第五,要有定力,你不能光顧自己爽,把她弄到高潮才是你的最高境界。如果她能有三次以上高潮,報警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第六,這第六,你能補充嗎?」我盯著她的小臉看著。
她的小臉羞得通紅。
我在她耳邊輕聲說道,「不好意思,我只是想把他們嚇走。」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似乎和善了許多。
「誰做得到這些,你能嗎?」柱子問道。
「我,我當然能。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裝著要走。
「哈哈,我剛才就在琢磨,就算我們把她弄到高潮,她事後不報案,可憑什麼你就不會報警呢?」尖嘴大叔笑道。
「我,我也不報∼」
我盯著她的小臉看著。意思是,你不想報,我也不會報的。
「我,我不報,我為啥要報呢?弄得她老公知道有什麼意思?」我道。
「要你不報警,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這250圓我們三人平分、、」尖嘴大叔又道。
「我堂堂公務員,缺少這點錢嗎?」
「就知道你不差錢,這第二方案嗎,我們一起幹她唄∼」
「噢,你想封我的口,可我為什麼要幹她,我有女朋友的,雖,雖然我們分手了。」
「這麼漂亮的臉蛋,這麼雪白的奶子,你就不想玩,你是不是男人?」尖嘴大叔想激我。
「想玩又怎麼樣?」我看著她說道。
她頓時露出了極度失望的表情。在她看來,我與這兩個壞蛋沒有兩樣。
「想玩就能玩嗎?我還想搶銀行呢?」我繼續說道。
「怎麼不能玩,我們幹完,她就是你的了。你呢,正好把你的本事都用出來,把她幹爽了。看她還報警不。」
「憑什麼要我來把她幹爽,她爽不爽與我有一毛錢關係嗎?」
「怎麼沒關係,正如你說的,不把她弄爽了,她就會事後報警。」
「不把你拉下水,你也會報警。」柱子道。
看來他也明白過來了。
「我絕不幹犯法的事!」我大聲地說道。
「那好吧,我們先姦後殺。」尖嘴大叔道。
「殺誰?」
「你倆呀!」
「為什麼?」
「滅口呀,笨蛋。」
「大叔,你不能開這樣的玩笑。」
「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嗎?」大叔玩弄著手裡的尖刀。
我這下有點怕了,轉頭去看雨瓊,她一臉的煞白。
「那你想要怎樣?我,?」
「你不是老是喊和平解決嗎?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你也來幹她一把,我們幹完,她就是你的了,把她幹的爽爽的。她不會報警,你也不會報警。」大叔一臉壞笑。
「然後呢?」我問道。
「我們平安離開,你呢順便玩了個少婦;她、她也不是什麼黃花閨女了,就當他老公多插了她幾次,如果你真像你剛才說的那樣有本事,她也一定大爽了一把。大家都沒吃虧。」到底是老江湖,說起話來有條有理。
「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我轉頭兩眼盯著雨瓊,「我這算是乘人之危嗎?」
她把雙眼一閉,不作回應,只是死死咬著嘴唇,看出了她的憂傷。
「那也就只有這樣了∼」我歎了一口氣。
「我先來!」柱子把短褲也脫了,那雞巴像只剝了皮的兔子,高高的挺著。
雨瓊也一定看到了,臉蛋又變得通紅,她又把眼光移向我,幽幽地看著我。
「沒聽我剛才的話嗎?先去洗一洗,把你的雞巴好好搓一搓再來!」
「對,快去。」大叔道。
「告訴他,你的沐浴香波在那裡?」我拍了拍她的胳膊。
「就在浴室的架子上。」
「聽到沒有,好好用香波洗一下!」
「必須的。」柱子答道。
一會兒從浴室裡還傳來了水聲,還有歌聲。
老江湖嘿嘿的笑著,大口地喝著紅酒,那拉菲的瓶子已經沒多少酒了。
「你,還行嗎?想幹也快去洗一下。」我道。
「不瞞你說,今天喝大了,恐怕還真的不行了。」他摸了摸檔部。
「可不玩又不甘心,就讓我摸兩把。」他搖晃著走向雨瓊。一手抓住了她左乳,另一隻手抄向襠部。
雨瓊不敢看他,幽幽地望著我。向我投來了求救的目光。
「大叔。」我把他拉開到一邊,「既然今天不行,那就算了吧。」
「這樣,我這裡也有250塊錢,一併給你,等你晚上酒勁兒過去了,到發廊找個小姐,花100塊做個全方位服務,不是更美嗎?」
「有道理,說話算話?」老江湖笑了。
我當即掏出250給了他。
我回頭看雨瓊,她也正好看著我,那是一種讚許,感激目光。
乘這老江湖又捧起了酒瓶。我俏俏靠近雨瓊。撕掉了她嘴上的貼紙。
「你放心,等會兒,我會想辦法的∼」
她微微笑了一下,表示謝了。
「如過他們硬要我上,我就在外面裝裝樣子,我不會真的插你的,放心。」
「嗯,謝謝你。」她點了點頭。
「為了要裝的像,我可能會親你的,玩弄你的乳房,你不介意吧?」
她的頭動了一下,像是點頭又像是搖頭,小臉又紅了起來。
我又到後面鬆開了綁繩。
「一切都會很快過去的。」我在她的白嫩的手臂憮摩著綁繩的痕跡。
柱子小跑過來。又要動手了。
「等一下,我們倆只有一個人能真的幹!」
「什麼意思?」柱子急不可待。
「一個人幹是強姦,兩人以上幹那就是輪姦,罪加一等的!」
「你不會是想一人獨吞吧?」
「不如我們分分工,一人玩上半身,一人玩下半身。」我道。
「那具體咋玩呢?」柱子問道。
「玩下半身就是插B;玩上半身麼是親嘴摸奶,由你挑。」
「我要插B。」柱子很乾脆。
「好,但你不許玩上半身,那裡歸我。」
「這樣好嗎?」我轉頭問雨瓊。
她搖搖頭。
「那,你是想我來插你嗎?」我盯著她的眼睛問道。
她還是搖搖頭。但看上去像點頭。
「不打緊,我會在上面親你,愛憮你的乳房,就讓他在下面他插吧,你就當做是我插你吧。」
她閉上了眼睛。也許她還是想由我來插她。
看著她極度羞澀的模樣,我對柱子說道:「我去洗個手,不許先動手,等我來了一起玩。」
「快點。」柱子對著雨瓊套弄著陽具。
我回來後,抓過雨瓊的手,偷偷把一把沐浴露抹到她手裡,然後讓她抓住了柱子的弟弟。
「來,讓姐姐摸兩下,試試大小。」
雨瓊想抽回自己的的手,被我擋住了。
「摸它!」我向她做了臉色。
到底是結過婚的人,聰明的雨瓊頓時名白了過來。順從著我的意思用手撫摸著柱子的陰莖,有結奏的搓捏了起來。柱子那經過這樣的玩弄,陣陣快感使他快活地叫了起來。雙手又伸向雨瓊的雙乳要捏。
「不行,上半身是我的地盤!」
我搶先扣住了她的雙乳,不讓柱子碰到他們。
開始只是想保護雨瓊,慢慢地,我的雙手也開始蠕動並加重了揉捏的力量,我滿意的看著她的神態,那本來就高聳的奶子此時更加柔軟挺拔了。
「啊∼」她竟然發出了快樂的呻吟。同時用雙手快速搓弄柱子的陰莖。
果不出我所料,雨瓊有結奏的擼動,加上沐浴露的潤滑,加上著雨瓊的呻吟。柱子體內的快感不斷增加,迅速衝向高潮。終於,陰莖在雨瓊手裡歡快地跳動了起來。不知是雨瓊是受到了柱子射精的感染,還是因為我的有效玩弄,感覺到她也像是動了情。她雙眼半開半閉,滿臉羞得通紅。
射精後的柱子,像只鬥敗了的公雞,呆呆地立在那裡。
「果不出這位大哥所言,你這過沒用的東西,還不快穿上衣服。我們走吧∼」尖嘴大叔道喝完了瓶裡最後的一滴酒。
「我們走了,她就全交給你了。」柱子還是有點不捨。
「好,全交給我,你們快走吧,再不走,樓上的那個警察要下班了。」
尖嘴大叔把我叫到門口,又反覆交代了幾句。
「評∼」門終於被我重重地關上了。我鬆了一口氣。回來把音響關小。
他們原想用音響蓋住雨瓊的叫聲,沒想到音響反爾把我引來了。
「小李老師,門鎖是好好的,他們是咋進了來的?」
「他們在門口說,高價收酒瓶子。」
「你這就讓他們進了了?你呀,太真了。」
「我錯了,我錯了還不行嗎?」
她一把抱住我,在我懷裡嗚嗚地哭了起來。
「這一切都結束了。」我在她背部輕輕拍著。
她緊緊地抱著我,那一雙豐滿的乳房頂住我的胸部。我心裡暗喜。
沒有了剛才的驚恐。她忽然之間在男人的懷中有了一種安全感,恍惚感覺依偎著自己的丈夫,享受著男人的味道,慾望漸漸開始發酵。
我試圖推開她,當然用力很小。
「抱緊我∼」
她下腹部也貼了過來。腳一掂,會陰部頂到了我高高挺起的陰莖。
「你這樣我要動情的。」我在她耳邊輕聲道。
「我不管,我要你抱我∼」
我抱起她來,走進臥室。原想順勢把她丟到床上,那知她摟在我頸部的雙手不肯鬆開,我一個踉蹌,撲到了她身上。頭一偏,下意識地將她的左乳頭含到了嘴裡。
「對不起,小李老師,我能這樣親你嗎?」我貪婪地吸著。
「叫我雨瓊吧∼」
「嗯,雨瓊,能親你嗎?」
「親吧∼」她一側身,把右乳頭塞到了我嘴裡。
那對夢裡憧憬過多少次的,正經賢惠的少婦的乳房,竟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等著我去愛憮。我的心中充滿了成就感。大千世界,有些事,不服不行啊。
我吻上她的嘴唇,挑逗著雨瓊的舌頭。
少婦的慾望在慢慢升騰,白嫩豐滿的身體還在我懷裡扭動著。
「我進來之前,他們有沒有玩弄你?」我問道。
「他們剛想要弄我,正好你敲門了,謝謝你。嗯,還要謝謝你的好辦法,讓柱子流掉了,要不好可怕。」
「也沒什麼好怕的,讓柱子在下面插你,我在上面玩你的乳房,親你的唇,也許更刺激,更爽。」
「不,不是的,我不想這樣∼」
「那你是想讓我在下面插你,柱子上面玩你囉?」
我心裡清楚,對於這個未經人事的少婦,情色羞辱能徹底打垮她的最後的一點自尊,盡情釋放出被挑撥出的少婦原始慾望。
「你,流氓∼」她羞的無地自容。
「你這樣的嫩逼閒著真是可惜了,以後我這個流氓天天來要來插。」
這種新的刺激使她進入癲狂的狀態。她從未像今天這樣需要男性。她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只剩下被情慾控制的誘人身體,任憑我的輕薄和玩弄。
「嗯,好,來插我吧∼」她自己脫了小內褲。
而剩下的事,只需猛烈的深插,就能徹底征服她。
——-
高潮以後,雨瓊羞怯地佔到我懷裡,低聲地說:「好舒服。你可真厲害,我真要被你玩死啦∼」
「以前沒這麼舒服過吧?」我很得意。
「從來沒有過,你太厲害啦!」她羞得粉臉緋紅。
「我也是,想再來一次嗎?」
「有點想,先歇會兒好嗎?」
「好的,吃點東西好嗎?」我有點餓了。
雨瓊一邊煮麵,一邊問我,「我們報警嗎?」她認真地看著我。
「什麼?你要告我強姦?」我緊張了起來。
「告你順姦!」她哈大笑了起來。
笑聲告訴我,她已被我從精神上、肉體上徹底地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