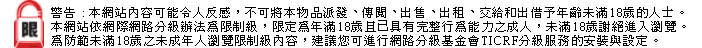女秘書的失身
五月的北京,天已經相當暖和。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袁芳坐在梳妝台前,慢慢地化着淡妝。雖然是星期天,她卻穿着奶白色的真絲長袖襯衫,灰黑色的西服短裙和肉色的長筒絲襪。中央商貿區辦公室小姐的標準打扮。袁芳沒有睡好,很早就醒來了。最近的許多事情讓她煩心,甚至恐懼,彷彿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就要發生,即將改變她的整個生活。
最近公司宣布結構重組,中國分公司雖然業績不差卻首當其衝。袁芳這個部號稱客戶服務部,技術員們都在外面跑,家裡也就七個所謂的白領麗人再加一個外方經理。外方經理名叫傑克,四十齣頭,調來中國部有大半年了,老婆卻一直沒跟過來。他能講漢語但不能讀寫。大家都說這人絕對是個好人,關鍵時刻肯為下屬爭利益,可就是有一個毛病,用技術員們的話講,叫作見不得穿裙子的。傑克不象其他老外那樣到三里屯酒吧里泡妞,他喜歡在寫字樓的白領裡面尋找艷遇,也不管人家是未婚姑娘還是有家的少婦,只要是穿套裙高跟鞋有幾分姿色的就糾纏上去。至於窩邊這七個辦公室小姐,他自然不會不注意到。半年前傑克上任不久,徐倩她們幾個北外畢業的就開始暗示,和老闆的關係不一般。會計部的沈芸曾悄悄告訴袁芳,說她聽到過傑克向公司其他外籍經理吹噓,一年內要把客服部七個女人全都搞上床。袁芳撇撇嘴,心想,別說還有自己,雅琴姐他就搞不定。
雅琴是她們七個當中最年長的,三十剛過,丈夫前年自費去了澳洲讀語言。雅琴一個人帶着四歲的女兒還要照顧公婆。在辦公室里袁芳和她談得來些。
傑克喜歡在辦公室獵艷,只要是穿套裙高跟鞋有幾分姿色就糾纏上去。
袁芳和公司里其他女孩兒不一樣,她只有師範專科學歷。正牌學校出來的,比如徐倩她們,就不怎麼看得上她。兩年前她走上社會,西郊一所小學教英語。
學校條件差,冬天教室里還要生火爐。寒假時她在公司里找了一份零時工,做文秘,後來就留了下來。去年夏天袁芳在地鐵里邂逅了她的白馬王子吳彬,今年春節雙方父母同意後他們就結了婚。兩人湊上所有的積蓄,加上父母的資助付了首期,在復興門小區貸款買了這套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安頓下來,算起來也不過幾個月前的事。袁芳並不太介意其他女孩兒怎麼看她,每天上班做好份內的事,下班就專心於自己的小家。吳彬是個儒雅的年輕人,瘦高的個子戴一副金絲邊近視眼鏡。他是人大的研究生,可惜專業不太好,畢業後因為成績優異留在了系裡做講師,也兼本科輔導員。他這個系沒什麼油水,就靠一份死工資,比起外企的袁芳少得多。小夫妻省吃儉用供着房貸,日子倒也過得平靜。袁芳沒有太多的錢,也不幻想太多的錢。她每天只化淡妝,穿中規中距的白領套裝和高跟皮鞋,和人到中年的雅琴倒有幾分相似。
守着身邊這樣的良家婦女,傑克自然不會放過,平時在辦公室經常有意無意地搭肩攬腰。只要沒有太過分動作,袁芳倒也並不表示反感,畢竟人家是老闆。
有幾次傑克試着表示想和袁芳發展那種親密的關係,都被婉拒了。去年公司的聖誕晚會上,袁芳一襲黑衣:黑色的弔帶晚禮服裙,黑色的長絲襪,和黑色的高跟漆麵皮鞋。傑克直勾勾地盯着姑娘裸露的雪白的雙肩,口乾舌燥。他假借醉酒身體不適,請袁芳送他回公寓。袁芳看看周圍沒有人注意他們,也找不到自己部里的人,只好扶着傑克離開喧鬧的人群。好在傑克的住所就在公司旁邊的外籍公寓樓里,沒費多大功夫傑克就被送進了房間。袁芳正要離開,傑克突然跪倒在她腳下,緊緊抱住了她的雙膝。姑娘又急又氣,拚命地掙扎,可哪裡爭得過健壯的傑克。眼看老闆把頭探到裙子里開始親吻薄薄絲襪包裹着的大腿,袁芳反到冷靜下來,停止了掙扎。感覺到意外,傑克疑惑地抬出頭來。袁芳用盡量平靜的聲音說:“傑克,我感謝你對我的好感,可是,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結婚了。我不願傷害我的未婚夫,你也不願傷害你的妻子,對嗎?”
傑克感到自己的頭腦在冷卻,雙臂不由自主地鬆了下來。袁芳轉身離開,輕輕帶上了門,只留下高跟皮鞋由近及遠裊裊的回聲。
“芳兒,快吃早飯!”
已經是吳彬第三次催促了。
“你先吃吧,我不太餓,一會兒在路上買點兒。”
袁芳依然靜靜地坐在梳妝台前,她的心裡亂糟糟的沒有頭緒。袁芳的家境不算太好,她從小是個獨立的女孩兒,了解她的人都說她外柔內剛,但是今天她感到從沒有過的無力和無助。她現在需要的是決定,可這個決定實在是太難。幾個星期來謠言紛紛,大家都在頻頻走動。到了上星期五,袁芳實在坐不住了。她敲開經理辦公室,要求討論下季度的工作計劃。傑克從文件堆里抬出頭,“芳,我喜歡直截了當。我知道你是為裁員的事,我也正要找你,可是你看,現在我太忙。這樣,你星期天到我家,早上九點半,沒人打攪。我的公寓不難找,你去過的。”
傑克站起來,扶住她柔弱的雙肩,“芳,不要憂慮。你是個稱職的女秘書,我是不會輕易放走一個女秘書的。”
袁芳的雙肩微微顫抖着,她不是個遲鈍的女人,她當然懂得傑克想要什麼,也知道如果拒絕意味着什麼。
整個下午袁芳一直昏昏沉沉。當她抬起頭時,辦公室竟然空空蕩蕩,大家早已下班回家。收好自己的東西,袁芳無精打采地走進樓道。這天她恰好穿了一雙平跟軟底皮鞋,空曠的樓道死一般寂靜,如同心情。當袁芳走過經理辦公室時,隱隱約約聽見彷彿什麼人在壓抑地急促喘息。她輕輕推開一條門縫,不由得呆住了:雅琴上身伏在寬大的老闆桌上,雙手緊緊扒住桌沿,豐腴白皙的屁股高高撅起,灰色的套裙,白色的內褲和肉色透明的褲襪被褪到膝下。傑克立在雅琴身後,褲子胡亂地堆落在腳上,結實的臀部奮力地前後衝刺,撞擊着女人成熟的身體。
袁芳悲哀着,為自己的同事,也為自己。
牆上的掛鐘敲響了十點。袁芳緩緩站了起來。她穿上外套和高跟皮鞋,拎了一副手袋,和吳彬招呼了一聲便走出家門。
站在地鐵車廂里,袁芳的頭腦慢慢清醒起來。地鐵,對於袁芳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幾年來,她幾乎每天都要在這裡捱過一兩個小時,當然,節假日除外。
在這狹小擁擠的空間里,伴隨着一個個疲憊的,無奈的,麻木的,而又頑強的面孔,熟悉的和陌生的,她成長起來,也變得堅強。對於平民百姓,生活和坐地鐵沒什麼兩樣,都是在黑暗的隧洞里隨着潮流往前奔,既不能改變方向,也無法控制進程,唯一能做的,是儘可能不要被人擠下車。袁芳就是這樣一個平民女兒,從遠郊考進城裡,又找到了令人羨慕的工作,然後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這一切都是那麼來之不易。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力,這就是神聖不可剝奪的人權。每個人都不應該輕易放棄自己奮鬥的果實,哪怕付出代價。
當袁芳再次沐浴在陽光下,她的腳步已經不再那麼沉重。九十年代初,北京的天空還是蔚藍色的,紫紅色的楊花已經落盡,鮮艷奪目的迎春正在怒放,和暖的微風拂過柳梢,也拂過姑娘的臉頰。袁芳已經做出了決定。她要捍衛自己的工作,捍衛自己的家,捍衛自己來之不易的一切。
如同傑克所說的那樣,他的公寓不難找。幾個黑人住戶走過樓道,看到站立在傑克門前的袁芳,做起了鬼臉,其中一人還衝她吹着口哨。袁芳沒有理會他們,這種騷擾,每個白領小姐幾乎每天都會遇到。然而,今天的,並不是出於對美貌的欣賞,而是一種嘲弄,因為最近他們看到太多的女人出現在這裡。他們知道這些女人敲響房門的目的,也知道房門關閉後,她們將自願地或被迫地做些什麼。
這些女人的年齡,容貌,衣着和氣質各異,而結果卻都是一樣的。可憐的外企白領麗人,合體的西服套裙和高跟皮鞋,臉上掛着職業而矜持的微笑,不菲的收入還有出國進修的機會,看起來是那麼風光無限,那麼令人羨慕。人們哪裡知道,她們當中多少人的日常工作,竟然還包括寬衣解帶,爬上軟床,把寶貴的貞操和美妙的肉體,奉獻給強壯而好色的老闆。袁芳不是不了解這些,可是她沒有更多的選擇。她理了理被風吹亂的發梢,平靜地按下了門鈴。
吳彬的客人已經陸陸續續地到了。今天他邀請了研究生時的同學和系裡幾個談得來的年輕教師。大家一直吵着要來看新娘子和新房子。袁芳推說老闆要和她單獨加班整理文件,趁着沒有其他人,還可以探問些公司裁員的內幕消息,吳彬也就沒有勉強。吳彬向大家介紹着他的新居,雖然不很大,卻被袁芳布置得舒適而溫馨。想到自己的妻子,吳彬內心充滿溫暖和驕傲。一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吳彬衝進地鐵站,車廂的自動門正在關閉,一個姑娘伸手為他擋住了門。那是一個清純的姑娘,明亮的眼睛充滿善良,白色的真絲短袖襯衫扎在剛剛及膝的黑色綢裙里,白皙勻稱的雙腿沒有着絲襪,腳上是一雙普通的黑色平跟搭袢皮鞋。那個姑娘後來做了他的妻子。
袁芳端坐在傑克的對面,外套搭在沙發背上,講述着她的職位對公司和她自己的重要。她沒有能夠講得太長,因為傑克打斷了她。“芳,你沒有理解我的意思,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我向總部遞交了報告,中國的通訊業市場比我們預想的大得多,一年以後,你能想象新增多少手機用戶?這不是幻想,我有全面的數據和圖表。七天!我整整準備了七天!沒日沒夜!”
傑克揮舞着雙臂,“我成功了!我說服了那些老頑固!服務部的規模,要能夠應付兩倍,三倍,甚至五倍於今天的客戶量。我的人,一個不能少!”
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袁芳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她望着這個有些激動的健壯的男人,心裡滿是感激和欽佩。幾星期的焦慮退潮般一下子全部消失,袁芳的眼睛變得無比柔和。覺察到這些微妙的變化,傑克站起來,擁坐在袁芳的身邊,輕輕攬住她纖細的腰肢。“芳,我會一直保護你的。”
不知什麼時候,傑克的另外一隻手搭上了袁芳的膝蓋,輕輕撫弄着。“芳,換個輕鬆的話題吧。今天要你來,不是為工作。我們相處得很好,你知道,我是希望和你有更親密關係,對,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床上的那種關係。”
袁芳只感到身體軟棉棉,頭腦暈乎乎的,沒有聽清楚耳邊低沉磁性的聲音到底說了些什麼。
當傑克的手觸摸到女人絲襪和內褲間裸露着的凝脂的時候,袁芳清醒過來,她撥開那隻手,猛然站了起來。“傑克,我不是那種女人!”
也許是起身太快,袁芳有點兒站立不穩,傑克用力一攬,她便倒進男人寬闊的胸懷裡。頭枕着結實的胸肌,嬌小的女人徒勞地掙扎着。她咬着嘴唇,緊緊夾住雙腿。傑克親吻着奶白色真絲襯衫繃緊的雙峰,一隻手慢慢撫過柔軟的高跟鞋面,薄薄的絲襪緊裹着的腳背,和同樣是薄薄的絲襪緊裹着的光滑勻稱的腿。這是他喜歡的那種女人!
是他喜歡的那種女人的裝扮!在他的家鄉已經愈來愈罕見的那種!“芳,我不會強迫你,我不會傷害我熱愛的女人。你知道,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太深,他只有進入女人的身體,才能把愛全部交給她。芳,我是那個男人,你就是那個女人。”
受用着甜言蜜語,袁芳感覺自己彷彿是飄在雲端。不知何時,一隻男人的大手,已經伸進套裙,從腰間探入她的內褲,撫弄着白皙的後臀。說不清是為什麼,恍恍惚惚間,袁芳輕輕地抬起了下身,小巧蕾絲邊內褲便被褪到了膝上。緊接着,一隻溫暖的手掌,順勢按住了濕漉漉的陰戶,老練地揉搓起來。袁芳扭動着,抗拒着,她開始不由自主地呻吟起來。
已經是酒飽飯足,吳彬在廚房裡切着水果。當年的下鋪老大走進來,一面剔着牙,一面說:“老三啊,這麼好的弟媳婦兒,你可得給我看緊了。這兩年去外企的多了,那裡面啊,不說了。”
吳彬一愣,說:“你說的是港資台資吧,小芳是美資的,國際大企業,很正規的。”
“這年月,什麼貓資狗資的,”
不知何時,老四踱了進來。“我們二輕局,怎麼樣?純正中資。組織部的高老頭兒,女大學生來一個玩兒一個,來一對兒玩兒一雙。”
看到吳彬臉上有點難看,老大用眼神制止了老四的進一步發揮。“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小芳是規矩人家出來的,跟她們不一樣。”
吳彬辯解着,心裡隱隱約約開始不安起來。
吳彬不可能想象到,他的新婚妻子今天的加班,是在建國門外那幢高級公寓的一個豪華套房裡。套房內間的卧室,暗紅色的落地窗帘擋住了午後的驕陽,也擋住了整個外面的世界。寬大的席夢絲床上,是柔軟潔白的厚厚的純棉布被單,刺繡的白色牡丹花依稀可辨。床頭的壁燈已經被調到最低,柔和的暗黃色光韻曖昧地注視着床上赤裸的男女,也注視着地上零亂的男人的襯衫,長褲,三角內褲,短襪和皮鞋,還有女人的真絲襯衫,西服套裙,鏤花的胸罩和蕾絲邊內褲。男人的身體是強壯的古銅色,更襯托出女人的嬌柔和潔白。一根粗長的陰莖直撅撅地,在女人的兩腿間蕩來蕩去,紫黑的龜頭已經滲出液體,在昏暗的燈光下閃閃發亮。
傑克半跪着俯在女人的身邊,靈巧的唇舌熟練地吻過女人身上每一個山丘,每一塊平野,和每一道溝谷,一遍又一遍。女人情不自禁地呻吟着,緊張的身體在慢慢鬆弛。傑克嘗試着把自己粗壯的下體送到女人的唇邊,女人側過臉微微蹙眉。
他沒有堅持。
當女人的呻吟愈來愈急促,傑克下腹的那團火已經燒到了胸口,他知道應該開始了。傑克直起身,輕輕分開女人的雙腿,跪在其間。女人的腿間柔軟光潔,沒有一絲體毛,嫩紅色的蜜唇微微顫動,春水盈盈。傑克粗壯堅挺的陽具老練地抵住了女人的桃源。深深一次呼吸,他俯身抱緊女人光滑的肩背,結實的臀部緩緩地向前頂去。當傑克慢慢侵入女人的身體,女人顫抖起來。“不,不要,我有丈夫。”
彷彿恢復了理智,女人的雙手抵住男人肩,像是在試圖推開,又像是在試圖拉近。
“親愛的,我就是你的丈夫。”
終於,傑克粗壯的陽具,整根沒入女人的身體。“噢,好舒服。”
女人緊密陰道讓他無比快樂,從未有過的暢快淋漓傳遍全身。
袁芳知道該來的終歸要來,她只能咬緊嘴唇,抬高下體,迎接命運的安排。
當巨大的充實和痛楚同時襲來,袁芳情不自禁發出一聲輕呼。從未有過的體驗,說不清是失身的羞愧,還是偷情的愉悅,佔據了她的整個身心。袁芳感到冥冥中無形的力量脫起她的腰臀,向上,向前,勇敢地迎接着陌生的挑戰。男人在抽送,女人在迎合。隨着一次次的探索和包容,陌生的肉體漸漸相互熟悉。痛楚在消失,留下的只有全新的刺激和無比的歡愉。吳彬的身影模模糊糊一晃而過。
斜陽掛在西邊的樹梢上,電報大樓的陰影拖得老長。
吳彬的客人三三兩兩地離去了,他的心漸漸緊張起來。與老大和老四的交談使他不安。他知道,他們所講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舊的道德正在破碎,新的道德還沒有成型,可以說,這根本就是一個無道德的時代。每一個人都無時無刻不在經受各種誘惑,有人隨波逐流,有人潔身自好。生活的重壓之下,人們抵禦誘惑的能力,到底能持續多久?吳彬不敢再想下去,他開始撥打妻子辦公室的電話,一遍,兩遍,沒有人接聽。這麼久了,她是和那個好色的老闆單獨在一起的!吳彬的心開始慌亂,他變得不知所措。突然,眼前一亮,對,平時妻子出門都是帶手機的。
一陣陣手機的鈴聲在客廳里執着地響起來。席夢絲床上激烈交纏中的赤裸男女,一個老闆,一個女秘書,是不可能也不情願注意到的,因為在這間密不透風的卧房裡,人世間的其它一切都不再存在。溫暖潮濕的空氣中只回蕩着男人粗重的喘息,女人嬌媚的呻吟,軟床不堪重負的吱吱嘎嘎,和濕漉漉的肉體相互撞擊發出的啪啪的聲響。傑克感到自己充滿了激情,彷彿回到他十六歲的那個夏天,一個雷雨天的傍晚,在家鄉老宅悶熱的閣樓上,他,和鄰居十八歲的愛瑪。一樣的柔情,一樣的溫存,只是,胯下這個女秘書的身體,更加溫暖,更加濕潤,也更加緊密。他知道,自己體內那團火即將迸發。傑克開始毫無保留地最後衝刺,越來越快,越來越猛。隨着深深的一次插入,一股滾燙精液直射入女人的身體。
傑克繼續奮力抽動着,任憑精液狂噴亂射。
袁芳緊抱着男人寬厚的臂膀,隔着薄薄的肉色絲襪,她的雙腿死死纏繞着男人的腰身。一隻高跟皮鞋還勉強掛在緊繃的腳趾上,隨着交媾的節奏晃動着,而另一隻早已不知去向。她感到自己彷彿化作了身下一朵絢麗的牡丹。男人每一次的衝撞和自己每一次的迎合,都催開一片花瓣,而每一片花瓣的綻開,又使自己更加絢麗。男人的喘息越來越急促。腳上的高跟皮鞋滾落下來。終於,所有的花瓣一齊綻放,美麗的光彩照亮整個房間。袁芳緊緊擁抱着身上的男人,一股股濃濃的瓊漿,注入她的花蕊,也注入她的心田。
當疲憊不堪的袁芳回到自己的家中,外面已是華燈初放。她不記得是怎樣推開壓在她身上沉重的男人,也不記得是怎樣堅定地回絕了那個男人再次的邀請,更不記得是否又遇到過那幾個黑人鄰居。袁芳躺在浴缸里,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着自己。她的身體沒有變化,似乎更加飽滿。袁芳感到自己什麼也沒有失去,又好像失去了很多很多。吳彬沒有察覺到妻子細微的變化,他靠着門框絮絮叨叨地講述着聽來的小道消息。“你知道吧,社科系的王博士,就是前年在亞運村買房的那個,老婆丟了工作,現在別說房貸,連物業都快交不上了。”
吳彬的聲音驕傲起來。“我跟他們說了,我就不怕。我老婆,本事大着呢!”
兩顆晶瑩的淚珠,滾落在袁芳的臉頰上。
結構重組風波終於過去了。除了客服部,其它部門都被砍去百分之二三十。
沈芸離開了,她決定去闖深圳。袁芳幫着她把行李拎上火車,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芳兒,千萬別哭,我膽小。”
沈芸摟着袁芳的肩,“唉,我算看透了,這世界上的老闆絕大多數都是欺下媚上保自己的。你們傑克屬於稀有動物。不過,芳,不是我打擊你,傑克干不長,他得罪人太多,還是上邊的人。”
見袁芳有點怔怔的,她俯到袁芳的耳邊,“哎,他把你弄上床了沒有?”
袁芳心裡一慌,趕忙岔開說:“去你的,你才被弄上床了呢!”
兩個女孩笑起來。年輕是多麼美好。
北京的春天是短暫的,迎春花很快就謝了。槐花開了,槐花又落了,樹上的知了便不知疲倦地唱起歌來。銷售部的業務果然多起來,連家裡的姑娘們也要開始跑外勤了。
這天晚上,吳彬幫着妻子收拾好行裝,兩人洗洗便早早上了床。黑暗中,小夫妻倆親吻着做起愛來。最近袁芳要的特別多,弄得吳彬有點力不從心。袁芳全身赤裸,躺在床上,翹起白嫩渾圓的屁股,兩條玉腿高高抬起,搭在丈夫的肩頭。
吳彬雙手撐着身子,擺動腰胯,不住地撞擊着妻子。“啊!哦!啊!”
袁芳呻吟着,渴望着,雙手緊緊地扒着丈夫的臀部,嬌媚而急迫。吳彬知道,妻子是想要更加深入些。他賣力地動作着,很快便一泄如注。
兩人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芳兒!”
“嗯。”
“你真的是和徐倩一起陪你們老闆出差?”
“當然。怎麼啦?不放心了?”
袁芳笑着安慰自己的丈夫,“徐倩那種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不會給別人機會的。”
“不,不,”
吳彬忙不迭地解釋着,“我是說,徐倩就是說話比較不注意,你別跟她計較,傷着自個兒。”
雖然袁芳儘力忍讓,她和徐倩的矛盾還是在最後一天的上午爆發了。事情的起因不大,無非是關於文書上的一點紕漏,徐倩便不依不饒起來。“就你那點兒本事,誰不知道啊?也就教教小學四年級。整天假模假式的,蒙誰呢你?”
袁芳不大喜歡別人總提起過去這段經歷,“我教過小學怎麼了?也是憑本事吃飯!不象有的人!”
“憑本事吃飯?你要是憑本事,早就裁了你了。我看恐怕是那種本事吧。”
徐倩的嘴是有名的尖刻。“你胡說!你出去!”
袁芳氣憤至極。“你才該出去!你出去!”
窗外的知了還在叫個不停。望着僵持中的兩個女人,傑克不知所措,“好了好了,女士們,你們都不出去,我出去。”
他馬上就後悔莫及,因為,兩個女人都轉向了他。
“傑克,你今天要說清楚,你是要她出去,還是要我出去?”
徐倩首先發了難。
“對,說清楚,到底是誰的錯。”
袁芳已沒有退路。
兩個倔強的女人對峙着。袁芳的信心其實並不足。想着工作已經結束,今天她隨意地穿了一件白色碎花的連衣裙,腳下是白色的皮鞋。反觀徐倩亭亭玉立,白色的襯衫領口打着絲結,深藍色的西服短裙,黑色的絲襪與高跟皮鞋,氣勢顯然勝出許多。
傑克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然後又望望這個,再次望望那個。終於,他慢慢走到徐倩身邊,輕輕扶住她的肩。袁芳看着自己的鞋尖,羞愧得無地自容。她不恨徐倩,只恨自己,為什麼不記住吳彬的話,非要和徐倩計較。她感到旋暈,她一秒鐘也撐不下去,她要自己離開。
然而,真正離開的卻並不是袁芳。
“倩,你太激動了,這對你不好,你暫時離開一會兒,可以嗎?”
傑克充滿歉意的聲音。
片刻的沉寂。高跟皮鞋憤怒的踏地聲。門被重重關上了。留在房間里的一對男女同時撲向對方,久久地擁抱着,親吻着,彷彿世間的其它一切都已消失,直到急促的電話鈴聲把他們驚醒。
“是我的。”
袁芳紅着臉,推開男人,走到窗前的桌邊,打開手機。
吳彬今天起得很晚,學校已經放暑假,不用去坐班。他坐在床上,拿起了電話,他要打給他的妻子。其實也沒什麼事,只是想知道事情辦得怎麼樣了,在南方身體適應不適應,有沒有和徐倩鬧彆扭等等,最後順便問問天氣如何,晚上的飛機會不會晚點。
袁芳應付着吳彬。想到剛才失態,她愧疚萬分,多虧了吳彬的電話,否則,她不敢想下去。到此為止,必須到此為止了。她和徐倩不一樣!她不是那種隨便的女人!然而,傑克的想法不一樣。不知何時,他已經立在袁芳身後,雙手抱住女人的腰,輕輕地吻着女人的耳垂。他知道,女人在和她的丈夫通話,這使他格外興奮。他把前胸貼緊女人的後背,暗暗用力,女人的上身漸漸伏在桌上,撅起的臀部,不可避免地頂住了他的下體。
吳彬感到電話中的妻子心不在焉,呼吸也開始不流暢起來。
他關切地問:“芳兒,是不是空調太涼,傷風了?”
“嗯,可能是,我想歇會兒了。你放心吧,天好着呢,飛機不會誤點。嗯,好,你來接我,晚上見。”
袁芳放下電話,撐着桌子想直起腰來,但是沒有成功。男人的力氣實在是太大了。袁芳正要開口喝斥,眼前一暗,裙子被掀開蒙在了頭上,緊接着,她感到下身一陣清涼,鏤花內褲被褪到了膝蓋。袁芳非常惱怒,她扭動身體掙扎着,可是,雙腿懸在桌邊,只有鞋尖勉強着地,她完全用不出力。她聽到身後窸窸窣窣的聲音,她知道,是男人在解開皮帶褪下褲子。傑克看着女人白嫩的屁股扭動着,對於他彷彿是一種邀請。他雙手把住女人纖細的腰肢,晃了一晃,挺起早已經怒不可遏的陽具,“啵滋”一聲,緩緩頂了進去。
放下電話,吳彬感到百無聊賴。他望着擺在床頭的小鏡框,鏡框里的袁芳身着白色碎花連衣裙,腳下是白色的皮鞋,甜甜地微笑着。那是去年夏天,吳彬在頤和園拍攝的。在那裡,吳彬第一次吻了心愛的姑娘,也第一次撫摸了心愛的姑娘的大腿。姑娘嬌嗔地埋怨着跑開了。吳彬微笑着,他感到小腹陣陣發熱,手情不自禁地伸向下體,握住了自己的男根,輕輕套弄起來。
袁芳不喜歡後進的體位,她曾經告訴吳彬,說她需要看得見愛人的面孔。可是今天,一波又一波的快感很快便沖淡了被征服屈辱。想到徐倩也許就在門外,也許隨時都可能闖進來,袁芳感到格外的興奮。她努力地踮起腳尖,配合著男人的衝刺,彷彿徐倩正幽怨地站在旁邊。她的身體好像山間一口間歇的清泉,泉水愈積愈滿,即將噴發。隨着瘋狂的抽插,一陣陣滾滾的熱浪,把袁芳送上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袁芳半張着嘴,驅動雪白的屁股,奮力迎接着男人的撞擊。太陽悄悄躲進一片雲彩,彷彿羞見這對激情中的男女。
傑克不需要愛人的面孔,他只要看見女人白嫩的屁股,豐腴的大腿,肉色絲襪根部的花邊和白色的皮鞋中踮起的雙腳。他一面抽送着,一面幻想着:美麗溫柔的女秘書跪在腳下,握着自己粗壯的陰莖,又吸又吮。伴隨着肉體撞擊和摩擦的“啪啪”聲和“啵滋”聲,傑克大聲喘息着,彷彿不久前他在凌晨的那次登山。
天漸漸亮了,而頂峰似乎還那麼遙遠。他奮力攀登着,終於衝上了巔峰。一輪紅日噴薄而出。袁芳緊閉雙眼,兩頰潮紅,喘息着,顫抖着,滴滴淌淌。
吳彬凝視着鏡框里的妻子,呼吸越來越急促,他的手飛快地套動着。終於,一道白色的弧線,從他手中划出,飛濺在潔白的床單上。
隔着千山萬水,吳彬和他的妻子,還有他妻子的老闆,同時達到了高潮。
美好的事物總是短暫的,而壞的預言卻常常靈驗。
一夜西風,地上便滿是金黃色的落葉。
傑克接到了調令,要他轉去加拿大的馬尼托巴省。大家都很惋惜和惆悵。傑克反到安慰大家起來,說上面這樣做也是為他考慮,至少他可以和老婆愛瑪靠得近一些。他默默地收拾行裝交接工作。徐倩幫他訂好了十二月二十五號的機票。
雅琴也要走了,她的丈夫不喜歡澳洲,辦了加拿大技術移民。過了年雅琴就要帶着女兒去全家團圓。
轉眼就是平安夜,窗外紛紛揚揚地飄起雪花,整個城市銀裝素裹。
吳彬不在家裡,他帶着學生們去延慶社會調查去了。袁芳一個人坐着,把家裡的溫度調得很高。她穿着白色的短袖襯衫,及膝的黑色綢裙,勻稱的雙腿沒有着絲襪,腳上是一雙普通的黑色平跟搭袢皮鞋。袁芳覺得這樣很輕鬆,好像又回到做姑娘的時候。今天她的心情有點緊張。傑克就要走了,也許今後不會再見到。
他所做的那些事,有條件的男人都會做,沒條件的男人都會想。傑克是個好人,臨走還不忘在職權範圍內給大家加了薪,對於那幾個有其它想法的技術員,他也一一準備了推薦信。
女人是感性的,她們難以忘懷的,往往不是對她們最真誠的男人,而是給她們最大肉體愉悅的男人。袁芳覺得應該單獨和傑克道個別,幾次在辦公室里可旁邊總有人。想下班後去他公寓,又怕再見到那幾個黑人,就這樣拖了下來。袁芳決定給他打個電話,可總是沒人接聽。已經是九點了,袁芳決定再試最後一次。
“嘟,嘟,嘟。”
她等了又等,還是只有留言。袁芳輕輕嘆了口氣,慢慢放下了電話。電話卻叮鈴鈴地跳了起來。也許是吳彬。袁芳接起話筒,心一下子狂跳起來。
“芳,我有一樣禮物想送你,不知是不是太晚了。”
“嗯,不晚,你現在哪裡?”
“就在你門外。”
袁芳跑去打開門,撲面而來的是一大捧鮮艷欲滴的紫紅玫瑰。沒有言語,只有緊緊的擁抱。不知誰先主動,兩人的衣衫從門廳一直撒落到床前。
當暴風驟雨終於平息,兩人疲倦地躺在床上。
袁芳枕着男人結實的胸肌,“傑克,愛瑪也去加拿大嗎?”
“我不敢肯定。你知道,她最遠就去過一次州府,不過,我最擔心的是她的哮喘。”
沒有再說話,過了一會兒,“傑克,你真的把我們七個都睡了嗎?”
又過了好長一會兒,傑克慢慢地說:“你問這些幹什麼?我已經厭倦了不道德的交易。芳,我向你保證,除了愛瑪外,你是我生命中最後一個女人。”
袁芳愣了一下,“告訴我我不會吃醋的,我又不想做你的妻子。”
“真的沒有,不過,只差一個。”
“是誰?別告訴我是雅琴。”
“當然不是。是徐倩。她一定要我先離開愛瑪。你知道,這不大現實。”
袁芳無言以對,她默默起身走進浴室清洗起來。
當袁芳在洗臉池前對着鏡子梳頭時,傑克站在了她的身後,張開雙臂環抱住她,“芳,我還想要。”
“去,快去洗洗。”
袁芳漲紅了臉推開他,躲出了浴室。
此時吳彬正坐在開往北京的長途汽車上。他的身邊堆滿了延慶縣的土特產。
他要給他的妻子一個驚喜。
傑克披着吳彬的浴巾走出浴室,他頓時驚呆了:一個光彩奪目的少婦,低頭側坐在床邊。床單已經換過,潔白得沒有一絲瑕疵,上面撒滿了鮮艷的紫紅色的玫瑰花瓣。少婦一襲黑衣,黑色的弔帶晚禮服裙,黑色的長絲襪,和黑色的高跟漆麵皮鞋。傑克盯着少婦裸露的雙肩,口乾舌燥。浴巾無聲無息地散開,滑落在腳下。
少婦站起來,款款地走近呆立着的男人,吻着他的前胸和小腹,緩緩地跪了下去。傑克感到眼睛有些發潮,陰囊和陽具分別被一隻柔軟小手握住摩挲着,然後,無比的溫暖,無比濕潤,腫脹的龜頭被含在了少婦的口中。“好粗大啊!”
袁芳跪在高大的男人面前,顯得那麼嬌小,男人的陽具又是那麼碩大。她只能含住淺淺的一段。她一面揉搓着陰囊,一面套弄着陽具的根部。昏黃的牆上,一個婀娜的身影長發飄肩,仰在男人的胯間擺動。袁芳感到嘴裡的東西愈來愈大,也愈來愈硬。
傑克的陰莖濕漉漉的,胸中的慾火越燒越旺,他開始大聲喘息。哪裡經受得起這樣的刺激!傑克按住袁芳的頭,粗大的陰莖更加深入,直抵咽喉。他完全陶醉在溫濕的快感中,按着女人猛烈抽動。快感一浪高過一浪。長發一次次甩起,又一次次落下,越來越急,越來越快。突然,一切都停頓下來。傑克緊抱住袁芳,死死抵在胯下。他顫慄着,一股濃濃的精液,直噴進女人的口腔深處。
袁芳喘息着,捧着雙手,滿嘴的精液緩緩流淌下來。
傑克憐愛地扶起袁芳,把她抱到床上。“芳,對不起,對不起。”
袁芳的裙子里沒有內褲。傑克躺下身,讓心愛的女人跨坐在身上,他扶着自己的陽具,女人慢慢地套坐下去。“噢,舒服死了。”
一陣顫抖,巨大的陰莖已經深入體內,強烈的刺激傳遍全身,袁芳不由得一聲呻吟。傑克握住女人的雙乳,恣意地揉捏着。快感,上下同步。袁芳微睜着眼,半張着嘴,陶醉在瘋狂的肉慾之中。
傑克托着女人的臀部,配合著女人的節奏動作着。他喃喃自語,“哦,芳,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
女人俯下身,熱烈地堵住他的嘴,“我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夜已深沉,曖昧的燈光下,一個美麗的身影在歡快地起伏跳動。袁芳感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燙,她努力着,很快就進入了瘋狂的境地。隨着一聲忘乎所以的大叫,女人的整個上身軟軟地癱塌下來。
當急促的喘息最終平靜下來,袁芳抽離了傑克的身體,翻身下來。她兩肘撐住上身,跪伏在鮮艷的紫紅色的玫瑰花瓣中,雙腿分開,裙擺自然地滑落腰間,白皙豐滿的屁股高高聳起,露出微微顫動的粉紅色的蜜源。傑克小心翼翼地進入女人的身體,緩緩抽送着,彷彿在擦拭寶貴的瓷器。女人的身體是那麼溫潤,緊緊地包裹着他的陽具,濕漉漉的肉體磨擦着,發出誘人的“啵滋”“啵滋”的聲音。他抬起頭,牆上的袁芳一身潔白的婚紗,甜蜜地依偎在吳彬的肩上,而吳彬默默地注視着床上激烈交媾中的妻子和另一個男人。傑克興奮無比,他抽送着享受着,體會着被女人緊緊包裹的感覺,他要延長這美妙的時刻。袁芳兩手緊緊揪住床單,身體奮力地前後搖擺,驅動着豐滿的屁股迎擊男人的衝撞。終於,濕潤的陰道又是一陣痙攣。緊緊夾着男人的巨棒,一股清泉噴出袁芳的蜜源。
傑克輕輕懷抱着袁芳。女人的身體還在抖動。
“芳,舒服嗎”“嗯,舒服。你還沒舒服呢。”
“我不要緊。只要你舒服,我就舒服了。”
女人的身體慢慢平靜下來,她爬起來,反身跨坐在男人身上,俯身又一次含住了男人仍然堅挺的陽具,深深地套動起來。“哦!”
一聲驚呼,傑克感到自己的龜頭,頂開了女人的咽喉。他撫摸着女人黑色絲襪包裹着的美麗的雙腿,抬起頭,舌尖抵住了女人水汪汪的蜜縫,吸吮着,一遍又一遍。
窗外的雪花還在靜靜地飄着,遠處隱隱約約傳來西什庫教堂的讚美歌聲。在溫暖柔和的燈光下,一對縱情的男女相互奉獻着,彷彿要到地老天荒。
門開了。吳彬到家了。
很多年以後。
五月的溫尼佩格,天已經相當暖和。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袁芳和雅琴坐在後院的露台上,慢慢地喝着茶閑談。因為是星期天,她們都光着腳,穿着寬鬆的襯衫和短褲。本地人標準的休閑打扮。兩個女孩在草地上玩耍。大的一看就知道是雅琴的女兒,小的很像過去的袁芳,除了頭髮是褐色自然捲曲的。不遠處傑克彎着腰正在修理破損的籬笆。
“芳兒,昨天徐倩打電話來,要走了你的伊妹兒。她總算釣着了金龜婿,是個海歸。兒子都上小學了。”
“嗯。那挺好的。找我有事啊?”
“想問問你們學校辦的暑期國際班的事。”
“幹嗎不去溫哥華多倫多?那兒多方便。”
“說是考慮過的,一來太貴,二來怕孩子學壞。放在這兒,還能讓你管着點兒。她現在賢妻良母着呢。”
雅琴湊近袁芳,壓低了聲音,“芳兒,你和吳彬還有沒有聯繫?”
“嗯,這兩年少了。他和他的一個學生結了婚,那女孩兒還行,在家待着,吳彬不讓出去上班。這幾年吳彬一直在忙着辦EMBA班,發達了。別的我也不清楚,你去問別人吧。”
袁芳不願多說,換了個話題:“你還記得芸兒吧,對,就是沈會計。她根本沒去深圳,火車上一個跑單幫的湖北佬搭上了她,到了武漢,她拎着行李就跟人下了車,漢正街上當起了小老闆娘。”
“什麼?不可能吧!”
雅琴驚訝地說:“我記着沈芸心氣兒高着呢。”
“什麼不可能?孩子都生了仨了!跑單幫的那點兒錢,全交了超生罰款。”
雅琴望着忙碌中的傑克,“芳兒,你看他的背好像有點兒駝了,你們不打算趕緊再要一個孩子嗎?”
袁芳搖搖頭,“這幾年他太辛苦了,賺的錢,一半繳了愛瑪的撫養費。”
一陣沉默,雅琴拉住袁芳的手。“芳兒,我看你這輩子怎麼盡還債了?在北京是供房貸,現在是供你的前任。”
袁芳笑了笑,沒有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