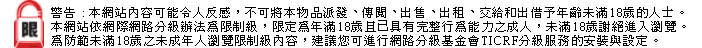靜悄悄的黎明
他在給她念雷蒙德卡佛,一個他崇拜的詩人的詩,她卻枕著他的枕頭睡著了。他喜歡大聲朗誦,這是他最拿手的愛好,念得非常好,時而低沈憂郁,時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頭櫃上取煙時停頓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過詩集。這個渾厚的聲音把她送進了夢鄉,她聽了幾分鍾,就閉上眼睛睡著了。
他接著大聲往下念。孩子們已經睡著很久了,外面,不時有車在路上擦出些聲音。過了一會他放下書,轉身伸手去關燈。突然,她像被嚇著似的睜開了眼,眨了兩三下。他注視著她。
在做夢? 他問道。
她點點頭,擡手摸了摸兩鬓。明天是星期五。公寓樓內所有的衛生清潔一整天都歸她管。他用手臂支撐著身體看著她,同時用閑著的那只手把床單抻直。她臉上皮膚光滑,顴骨突出;這顴骨,她有時會對她的朋友說,是從她父親那兒繼承來的,她有著四分之一的西南少數民族血統。
她剛要起身,他的手已經撫摸上了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在她的下身摩挲著…
“放開我,起來”她用手去推他,可卻已經被他壓在了床上,她的肌膚碰觸著他涼絲絲的皮膚,一種異樣的興奮在她心里升起,也不由得放開了推著他的手,他已經壓到了她的雙腿之間,她的一條腿已經屈起了,兩人的全身緊緊的靠在一起,他已經硬起來的下身在她的小肚子上硬硬的壓著……
“嗯…”他一邊親吻著她柔軟的嘴唇,下身微微一欠,陰莖就已經插進了她還是濕乎乎、粘乎乎的陰道,她哼了一聲,翹起來的腿一下就伸直了,他緊緊的壓在她的身上,下身用力的頂動著,很快她就已經受不了了,下身已經濕的水孜孜的了,哼哼唧唧不停的叫著……
“啊……嗯……”她筆直的秀發此時披散著垂下來擋住了她秀美的臉龐,卻能清晰的聽到她發出的誘人的呻吟,白色的睡衣亂紛紛的卷起著,一對豐滿的乳房正被他的大手揉搓著,白嫩翹挺的屁股用力的挺起老高,一根堅硬的陰莖正在屁股的中間來回的出入著,黑色的絲質內褲卷在小腿上,一段白得耀眼的大腿來回的顫動著,一只小腳用力的向腳心勾著……
她的呻吟越來越大,很顯然在他不斷的抽插下,就要到了高潮了,他的感覺也越來越強烈,手不斷的撫摸著她的屁股和乳房,下身緩緩而有力的動著。
她此時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屁股不斷的扭動著,他從緩緩的抽送到開始快速的沖刺,一波波的浪潮再次席卷了她的身體。
“啊……”她按捺不住的尖叫,屋里兩人皮膚撞在一起的聲音越來越快,終于在她一陣有節奏的高昂的呻吟之后,屋里的聲音停止了,只有兩個人粗重的喘息聲音……
良久,她說: 給我隨便弄點兒吃的,林,面包,牛奶。
他沒說什麽也沒做什麽,因爲他想睡了。但當他睜開眼睛時,她還醒著,正注視著他。
雅,你睡不著? 他非常嚴肅地說。 很晚了。
我想先吃點東西, 她說。 這兩天太累了,我的腿和胳膊都疼,還餓。
他重重地歎了口氣,翻身下了床。
他給她拿了下午剛買的速食面包,咬開一袋牛奶倒到大茶缸里端過來。她從床上坐起來,對他笑了笑,接過茶缸時往背后塞了個枕頭。他覺得她穿著這身白色的睡衣,看上去像是醫院里的病人。
真是個有趣的夢。
夢見什麽了? 他說,上床朝他那邊轉過身去,背對著她。他瞪著床頭櫃,等了一會兒。然后慢慢閉上眼。
真想聽嗎? 她說。
當然, 他說。
她舒服地靠在枕頭上,抹掉嘴唇上沾著的一個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個冗長的夢,你知道的,那種里面有各種複雜關系的夢,但我現在記不全了。林,我睡了有多久?其實,我想也沒什麽大不了的。總之,好像是我們在某個地方過夜。我們和孩子們都在那兒,待在某個類似小旅館的地方。在一個陌生的湖邊。你提議用小艇帶我們出去兜一圈。 她笑了起來,回憶著,身體離開枕頭向前傾。 接下來我只記得我們在上船的地方。結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點像張條凳,只夠坐三個人。你和我就誰該犧牲自己擠在船的后面爭了起來。你說該你,我說該我。但最終還是我擠進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擠疼了,我還擔心水會從船邊上漫進來。后來我就醒了。
真是個不一般的夢, 他應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覺得自己該再說點什麽。 你還記得妮嗎?阿德的老婆?她說她常做彩色的夢。
她看了眼手中的面包並咬了一口,粗糙並且甜的有些發苦,她慢慢的咽下去,用舌頭舔了一下嘴唇里面,向后靠在枕頭上。
你還記得那次我們在河邊過夜嗎,林?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釣到條大魚的那一次? 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還記得嗎? 她說。
她記得。過去幾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卻常想起它來。那是婚后的一兩個月,他們出去度周末。坐在小河旁,冰涼徹骨的河水里泡著一個西瓜,晚飯他們吃了午餐肉、雞蛋和罐頭魚,第二天早晨,蚊子把身上叮得到處都是紅包。但這是他們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她記得那晚他也給她朗誦了伊麗莎白勃朗甯的幾首詩。他們那麽酣暢淋漓的做愛,她的腿第二天動都動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釣到一條大魚,河對面路上的人都停下來,看他怎樣把魚弄上岸。
哎,你到底記不記得了? 她說,拍著他的肩膀。 林?
記得, 他說。他往他那邊稍微移了移。他覺得自己已經記不太清楚了。記住的只是她細膩的呻吟以及那時對人生和藝術半生不熟的見解,他其實很想忘掉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雅, 他說。
我剛拿到文憑,你還沒去上夜大, 她說。
他等著,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撐起來,轉過頭,目光越過肩膀看著她。 面包快吃完了嗎,雅? 她仍然在床上坐著。
她點點頭,把茶缸遞給他。
我把燈關了, 他說。
要是你想的話, 她說。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雙腳向兩邊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腳。他一動不動地躺了一會兒,試圖放松自己。
林,你還沒睡著,是吧?
沒有, 他說。 沒睡著。
那好,別在我前面睡著, 她說。 我不想一個人醒著。
他沒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兒稍稍靠近了一點。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他抓住她的手指,輕輕地捏了捏。只一會兒的工夫他的手又開始在她的身體上遊弋。
“你…你又要?”
他看著她美麗迷離的雙眼,也顧不得許多了
她有些拚命的推著他,可是他有力的胳膊緊緊地摟住了她的腰,她光光的小腳亂動著,卻又不敢大聲地喊,只有賭氣的掙扎著,握著他的手不讓他動,可是內褲還是被拉下了屁股,柔軟的陰毛都已經露了出來。
看著她眼里倔強的目光,感受著柔軟的乳房緊緊貼在身上的感覺,他有些無法自我控制了,手已經從兩人緊貼的下腹伸進了她的雙腿之間,摸到了溫軟濕潤的陰唇,她的雙腿緊緊地夾起來,彈性十足的雙腿夾著他的手
“不要啊,你放手…太晚了…”她的內褲在屁股下卷著,兩只小腳都已經踮起了腳尖。
他的手隔著薄薄的白色睡衣在乳房上溫柔的撫摸著,摸了一會兒就把睡衣撩了下來,一對顫巍巍的乳房就挺立在面前了,他一邊開始吸吮乳頭,一邊手繼續摸著她的下身,她的身體抖了一會兒,輕輕地從嗓子眼里歎息了一聲,就把腿微微的岔開了,隨著他的手的撫摸,她的氣已經開始喘不勻了。
他慢慢地把下身挺了進去,感受著下身濕軟的感覺,舒服的歎了口氣,雅的陰道從前到后都緊緊的裹著陰莖,抽動起來從前到后都有感覺,她的兩腿這時都屈了起來,腳跟緊緊的瞪著床單,腳尖都翹起著,長長的陰莖讓她的心都有了懸起來的感覺,下身更是被頂的又酥又麻,每抽插一次,她的屁股都緊緊的收縮一次,兩手不由自主地扶在林的腰上,深怕他用力的頂她。
“啊…嗯……噢…”她咬著嘴唇,晃動著頭發,伴隨著男人的抽送,不由得從嗓子眼發出了抑制不住的聲音,渾身也開始變得滾燙,乳暈變得更加粉紅,一對小乳頭堅硬的挺了起來。她渾身軟軟的癱軟在他的身下,每動一下都渾身顫抖,嬌喘連連的不斷叫著。
恍惚中,她一下看見了床頭的相框,照片里的她穿著潔白的婚紗,一臉幸福的看著文質彬彬的林。她的心里一陣疼痛,這時林把她翻了過來,讓她跪在床上,他扶著她翹起的屁股,在昏暗中抱住她,插了進去,黑暗中享受著火熱的肉體,她的雙手緊緊的抓著床單,屁股翹得很高,兩個人抑制不住的粗重的喘息在屋里回蕩。一種極致的快感幾乎爆炸在了她的身體里,她在林終于射出精液的瞬間,整個人都挺了起來,渾身不斷的顫抖,下身更是濕乎乎的一大片,等到他抽出陰莖,起身把她抱著放到床上時,她感覺頭昏昏的,渾身軟軟的一點力氣都沒有,這時才感覺到腿一陣陣的酸痛,膝蓋有一種麻酥酥的刺痛。過了好一會兒,她搖了搖身邊昏昏睡去的林。
林?親愛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 她說。
天哪, 他輕聲說道。 我剛才都睡著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說會兒話,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別疼。
他轉過身來,開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著了,手還放在她的臀部。
林?
怎麽了?雅,告訴我怎麽了。
我想要你幫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 她說,轉身面朝上。 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
黑暗中他快速地睜開眼,又閉上,最終用胳膊支撐起自己,看了看鍾。他把枕頭涼的那一面翻上來,又躺了下來。
她說: 我希望你願意聊一會兒。
好吧, 他說,沒有動。
你只要抱著我,讓我睡著了就好。我睡不著, 她說。
他轉向另一側,她轉過身來用胳膊摟住他的肩膀。
林?
她用腳趾頭碰了碰他的腳。
跟我講講你喜歡的和不喜歡的東西。
現在想不起來, 他說。 願意的話你可以告訴我你的。 他說。
如果你保證告訴我的話。願意保證嗎?
他碰了碰她的腳。
好吧 她說,仰面舒服地躺著。 我喜歡好的食物,像排骨和乳酪蛋糕那樣的東西。我喜歡好看的書和雜志。 她停住了。當然,沒有按照喜歡的順序排。如果要按順序排的話我得想一想。她把腿擱在他的腳踝上。 我喜歡晚上睡晚點,第二天早上賴在床上不起來。我希望我們能經常那樣,而不是偶爾的一次。我還喜歡做愛,喜歡在不經意時被愛撫。我喜歡看電影,過后一起吃冰激淩。我希望每月至少去看一次電影。我希望孩子們能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們需要時不用等就可以給他們買衣服。阿白現在就需要一套過節的衣服。我也想給磊磊買一套新的衣服。他畢竟是雙胞胎哥哥。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實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們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隔幾個月就得搬次家。這是最大的希望了。
她說, 我希望我倆能過一種踏實的生活,不用去擔心錢和賬單之類的東西……你睡著了。 她說。
……沒有。過了小會兒,他說。
我再也想不起什麽了。該你了。告訴我你喜歡什麽。
我不知道,好多東西。 他咕哝了一聲。
嗯,告訴我嘛。我們不就是說說而已嗎,是吧?
我希望你別煩我了,雅。 他又轉到他那一側,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轉過身來,緊貼著他。
林?
天哪, 他說。接著又說: 好吧。先讓我伸伸腿,我好醒過來。
過了一會她說, 林?你又睡著了? 她輕輕地搖了搖他的肩膀,但沒有回應。她靠著他的身體躺了好一會兒,試圖入眠。起先她很安靜地躺著,一動不動地靠著他,均勻地小口呼吸。但她睡不著。
她努力不去聽他的呼吸聲,那讓她覺得不舒服。呼吸時他鼻子里發出一種聲音。她試圖調節自己的呼吸,讓呼氣和吸氣合上他呼吸的節奏。但沒用。他鼻子發出的這種細小的聲音讓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她又翻了個身,用屁股抵著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牆。她聽見兩個人走來,在上樓梯。有人在開門前發出一個嘶啞的膩膩的笑聲。然后,她聽見椅子拖過地板的聲音。
她又翻了個身。隔壁有人沖抽水馬桶,稍后,又沖了一次。她又翻了個身,這次面朝上,嘗試放松自己。她想起了在一本雜志上讀到過的文章:如果身體所有的骨頭、肌肉和關節都能完全放松的話,睡眠一定會降臨的。她長長地呼了口氣,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地躺著,手臂伸直放在身體的兩側。她盡量放松自己,閉上眼睛,又睜開來。她想著嘴唇前面的床單上卷放著的手指。她伸出一根手指來放在床單上。她用拇指摸了摸無名指上的結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側面,又翻到正面。她開始感到恐懼,在一種莫名的焦慮中,她祈禱能夠入眠。
求你了,老天,讓我睡吧。
她努力要睡著。
林, 她小聲說道。
沒有回應。
她聽見隔壁房間里一個孩子翻身時碰到了牆。她聽了又聽,但再沒有其他的聲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傳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頭離開枕頭,嘴貼在床單上,哭了起來。她哭了一會兒,然后爬到床腳處,從那兒下了床。
她在衛生間洗了臉和手。她刷牙,一邊刷一邊從鏡子里端詳自己的臉,她又哭了。
過了一會兒,她去查看孩子們。把小兒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蓋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廳里,坐在那張大椅子上。不時有輛車從外面的街上開過,她會擡起頭。每當車子開過時,她都要聽著,等著。
曙光初現時她站了起來。她來到窗前。樹木和街對面那排兩層高的公寓樓在她的注視下顯露出它們的形狀。天空變得更白了,光線在急劇增多。除了因爲孩子中的這個或那個而早起外,她確信沒有一次像這樣仔細的端詳著日出的過程。她從未在讀過的書和看過的畫里了解到日出會是這麽的可怕。
她等了一會兒,感覺到了黎明刺骨的寒冷。她掖緊睡衣的領口。空氣又濕又冷。周圍的景象漸漸顯露出來。她一點點地看過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路口閃爍的紅燈。
她拉上窗簾回到幽暗的臥室。他在床中央躺著,被子纏在肩膀處,頭的一半壓在枕頭下面。沈睡中的他顯得絕望,緊咬牙關,胳膊直挺挺地伸過她這邊的床。在她的注視下,房間變得非常明亮,床單在她眼前越來越白。
她濕了濕嘴唇,發出了一點粘滯的聲音,跪了下來。她伸出手攤在床上。
天呢,她說。有人能幫助我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