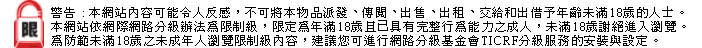附體記41-45
第五部
羽翼初豐
四十一、洞房花燭?本部簡介?
東府擄了陸小漁來為老太君沖喜,洞房之中一龍二鳳、妻妾同眠,李丹好不得意,沒想到新夫人陸小漁也不是普通人物,大紅燭前與李丹約法三章,洞房喜榻上合逗浣兒,看來男人夢想的閨閣秘戲不遠矣……「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五陰熾盛」八苦交攻,令人聞之色變的怨憎會盯上了賈府,李丹本以為是自己收留連護法引來禍端,沒想到賈似道才是怨憎會的真正「孽主」。
繼承了東府,又被捲入賈府的舊日冤仇,李丹難道就要被困在紅塵之中,做個逍遙貴公子了嗎?
四十一、洞房花燭胡九大叫:「過癮呀!過癮!好久沒遇見這樣的高手了!」
京東人語道:「奇哉怪也,玉淵閣能有你這樣的高手,打死我也不信,敢問閣下是否來自二郎山戰衣派?報上名來?」
吳七郎卻道:「不對,不對!二郎山戰衣派的怎敢戴二郎神面具?」
那人並不則聲,手上攻勢愈猛。
關西魔大叫:「十妹,你還在鬼畫符麼,我們快守不住了!這個陣沒有你的天羅豆,那還叫什麼『天羅陣』,人都要被你氣死!」
霍姑娘道:「來啦,來啦,我見他沒有傷人之意,不好意思以穢物汙他!」
關西魔道:「你見少主成親,也動春思了麼,既然瞧上了他,還不快把他留下,今兒一道拜堂,豈不省事!」
霍姑娘「哼」了一聲,隨手一揮,關西魔跳腳不歇,破口大罵:「小妮子果然動了春心,不幫自家,倒助外人!」
霍姑娘嗔道:「你再胡說,我讓小黑咬你!」隨手一撒,地面滾動著一粒粒的黑豆。
青袍人似知厲害,小心地避開地面黑豆,身法頓見滯澀。
霍姑娘隨著又連連潑撒,地面布著的黑豆愈多,忽而散處成陣,忽而貼地滾動,四面八方,遙相呼應,如受驅策,黑壓壓的令人生畏。
青袍人應敵之暇,不得不運足掌風,擊散身周黑豆,大受牽制。
胡九喝道:「藏頭藏腦,非奸即盜,給我現出形來!」長臂突探,去抓青袍人面具。
我與賈妃聽了胡九咋呼,不由吐舌相笑,再望去時,那青袍人不知使了甚麼手法,一手扣住胡九一臂,拽著他東扯西晃,另一手揚掌拒敵,卻也無暇擊傷胡九。
胡九被他拖住身子,狼狽且怒:「喂,拉拉扯扯,什麼意思,有種你殺了我呀!」一邊叫嚷,一邊腳下亂跳,躲避地面黑豆。
吳七郎冷哼一聲,不顧身挨一掌,硬向前衝,青袍人陡然丟開胡九,「彭」的一聲,氣勁交激,結結實實與吳七郎對了一掌,吳七郎連退數步,臉色煞白:「好,好掌力……」委身一倒,旋又支住身子。
胡九道:「七哥,你……」要去扶他。
吳七郎擺手道:「沒事。」退出陣外,眼朝青袍人盯去,面有訝色。
青袍人與吳七郎對掌之後,稍不停歇,又擋擊他人前攻,揮灑無滯。
東府眾人齊聲怒喝,全力圍擊,守住陣腳,不再退卻,一時身影縱起縱落,場中黑豆亦如於鍋中沸騰,起跳不定,時而濺出一粒,朝青袍人飛去。
青袍人應接不暇,呼嘯一聲,喊道:「陸閣主!」
陸幽盟知道他也抵擋不住了,無奈罷手,揚臂喊道:「小漁!莫慌!諒他們不敢難為你!你只記住,沒爹爹的話,什麼都不要依從!」
陸小漁聞聲,眼珠左右擺動,卻既無法瞧見陸幽盟,又無法答聲。我心中一動,暗笑:「她這樣子,與浣兒昨夜的神情真像!」
紀紅書笑道:「放心,我們不會難為她,只讓她作新娘子!」
陸小漁背向紀紅書,眼兒睜得更大更亮,彷彿是用眼睛在聽人說話,雖面露羞色,倒未見多少慌急。
青袍人清嘯一聲,陡然縱出陣外,飛身離去,陸幽盟也朝他追去,且行且回頭道:「小漁!我會讓藍藍來陪你!」
紀紅書道:「親家公!不要走呀。」
宋恣笑道:「改日新娘回門,再來請罪!」
陸幽盟一言不答,飄身而起,轉瞬便與那青袍人去得遠了。
賈妃怔了一會,低聲喃了句:「奇怪,那人身影,瞧著好眼熟!」拉著我悄悄退去。
一會東府有人來報,賈妃對陸幽盟鬧府一事,假著不知,含笑探問,聽說七郎受了傷,但並不嚴重,當下勉慰了幾句,隨即吩咐眾人加緊籌備婚儀,不可誤了時辰。
東府這邊張燈結綵,喜氣洋洋。眾女流聚在一個大屋子裡,勸說的勸說,打扮的打扮。一會傳來消息,新娘子聽是替老太君沖喜,竟答應拜堂成親了。我對陸小漁只遠遠望了幾眼,沒留多深印象,聽了只是微覺詫異,倒是浣兒那丫頭,昨夜才答應收她為妾,今日便喜事成真,很想瞧一瞧她此時臉上到底是何神色?
隨後沒多久,我也被人領去沐身換衣,待面上敷粉,身著喜服,回到染香廳,卻見棋娘竟也來了,不由又是心喜,又是扭捏。
棋娘含笑看我,打趣道:「這位新郎是誰?是筠兒麼,我怎麼不認得了?」
一名婦人足不停留地走到了我跟前,我正想此女怎地這般大膽?細一瞧,原來是濃妝已卸、面如新洗的紀紅書,她狠狠貪看了我一會,笑道:「這紅艷艷的衣裳一穿,再塗了丹粉,不像新郎,倒像新娘了!」
我心下暗恨,卻不便回嘴。
時下女子偏喜歡這種娘娘腔的文俊公子哥兒,連賈妃亦然,望著我的眼神大是讚許愛憐,其他僕婦更是藉著喜氣,放縱身份,七嘴八舌,一個勁兒地「像個俏女子」「活脫脫又一個美嬌娘」誇個不停,棋娘只掩嘴輕笑。
東府眾人在外忙乎,除我之外,染香廳皆為女眷,脂粉氣縈繞週身,我渾如墜入花陣,極不自在,有心跟棋娘說上幾句話,卻被幾人隔開,見她不緊不慢,遊過人群,到了賈妃身畔。
賈妃在高座上傾身,與棋娘交談,兩張春花秋月的面龐並湊一塊,容光對映,艷美如畫。棋娘容色雖出眾,妝扮並不醒目,適才混於眾女眷中,固然合宜,此時與華裳貴氣的賈妃兩相映照,卻也不失色幾分,倒另有一種含蓄之美。
棋娘不失本色,賈妃身居主位,俯臨滿廳女眷,與眾女主次相成,亦頗契合。
整個廳中,只有一人,獨枝旁逸,卻是雀使紀紅書。
她洗去鉛粉後,容貌中頓時透出遠靜之氣,與廳中熱鬧的氣氛頗不相符,身著道服的姿影亦卓然出群,似乎隨時都將淩虛飛起。年紀雖看上去比賈妃還大些,但臉上那股清麗之韻,揮散不去,讓人將她年華忘盡。
與卸妝前相比,她此刻像換了個人似的,唯一有些熟悉的,是她眼角漏出的幾許風情,讓我憶起她戲笑時的神態。
「大公子,我將如花似玉的美人兒給你請來,你該如何謝我呢?」
面容雖有些陌生,語氣腔調依然如故,望著眼前這道行深厚、春騷難掩的婦人,我只有認輸閃避:「啊,雀使,您辛苦了!一會請多喝兩杯!」
「我是那貪杯的人麼?」那語氣有些裝出的幽怨:「唉,為誰辛苦為誰忙呢?」
我咬牙切齒,假使真有那機會,將她撲倒,她定會一腳將我踢開!這只是個愛過嘴癮的騷婦,我拿她無可奈何。
吉時很快到了!有人過來催喚,新房設在水榭水旁的一個院子,這是因兩位新娘名字中都有水,乃八字缺水之故,宜臨水而居。
兩個新娘都披了紅蓋頭,身高差不多,吉服寬大,甚至無法從胖瘦上分辨哪個是浣兒,哪個是陸小漁。在一陣鬧哄哄中,我迷迷糊糊地牽了兩個新娘,拜過老太君,拜過娘娘,還要再朝棋娘磕頭,被她止住了。
這裡是男家,西湖阿九本來到了東府,婚事議定後,成禮之際,反倒刻意避開了,我竟沒見著。
婚禮倉促,沒多請外人,趕來赴宴的,大多是消息較為靈通的東府舊部,因此場面不大,卻格外嬉鬧無忌。
人不多,禮卻重。賈妃自有一份厚厚的大禮不說,東府舊屬送的都是罕見的奇珍異寶,棋娘以姨娘身份送了一份八色彩禮,另外借花獻佛,竟將青陽丹轉贈給了我。
我知道此丹乃助她破獄之用,推拒不受。棋娘卻道,所謂道獄,實乃她師尊留元長以自身的修為境界設障。當年,留元長因心傷其師白玉蟾水解,道心大亂,認為修道終是虛妄,欲棄道旁求。故種下道獄於唯一的女弟子棋娘之身,告戒她,若連他的道境都不能突破,那麼她苦心修煉也一樣白費,可以不必固執了。因此,破除道獄,主要靠領悟,青陽丹等外力,於她全然無益。那雲真子說得好聽,自己獲寶而不用,定然是無法融合此丹所攜的青陽氣,試丹之際,說不準還暗中吃了虧,才會那麼大方,贈施於她。而我得了天師的龍虎宗真氣,出身龍虎宗旁支的神龍門既於青陽山采練,與青陽氣定然易於融合,此丹或許於我能有助益。但試丹時,亦得加倍小心才是。
我聽了,心想棋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龍虎宗真氣未必能與青陽氣相融,我卻或許可以。當年師尊初臨青陽山,為其未曾遭人沾染的沛然元氣所誘,駐留數年,采氣修煉,險些煉成一塊木頭。原來青陽氣大部分為青陽古木吐息而成,木氣過燥,擾亂五行運轉,所採不當,不但無益修為,反會遭五行失調之劫。其後,師尊引辟鏡湖水入山,有了小鏡湖,以水養潤燥木,再改了入氣經脈,而後功成。
這番道理,我自不能跟棋娘細說,只點頭將青陽丹收下了。
棋娘最後低聲道:「筠兒,我有事須遠行,恐怕得有好一陣子,不能再見了。那邊府中最近多事,有何為難,你可讓東府眾人相助!」
我點頭答應,心道:「難怪這般著急,現在如此忙亂,她還將青陽丹也帶過來交給了我。」沈吟片刻,道:「爹爹很快就回來了,你不等他到了再走麼?」
棋娘面色微暈:「我幹嘛要等他?」
我心中一動,忽生奇想:「莫非她離府,倒為躲避賈似道?」
棋娘推了我一把:「那邊在喚你,不跟你多說了!」說著,轉身離開。
應酬過眾人,我牽著兩名新娘入了洞房。本以為妻妾分屋,我兩頭奔走,但看那引領婆子的處置安排,卻是一龍二風、妻妾同眠的格局!
我還沒發話,扶著新娘的一名紅衣丫鬟,滿面羞紅,急得口吃:「這……這怎使得?對我家小姐太……太不敬了!」
「姑娘,你不知道,別瞎說!」
那紅衣丫鬟還不依,竭力與婆子爭辯。只聽紅蓋頭下傳出一個柔和的聲音:「藍藍,不要胡鬧,聽嬤嬤安排好了!」
原來這紅衣丫鬟就是藍藍,我不由朝她多瞧了兩眼,姿色算得上周正,不能說有多出眾,但奇怪的是,她渾身上下,無不伶俐,該是什麼就是什麼,別有一番味道。想起昨夜拿她對浣兒說事,見了面卻毫不相識,不由暗下好笑,藍藍見我看她,瞪眼道:「看什麼!都怪你這壞蛋,將事情攪得一團糟!」
「藍藍!」
紅蓋頭下又傳來喝斥,這回聽出新娘的聲音低沈溫厚,不類少女的嬌脆,幾乎將我唬了一跳。
藍藍對我甚是不滿,白了我一眼。
主事的婆子見機扯了扯她衣袖:「姑娘,我們好出去了,讓新人歇息!」
藍藍大睜了眼:「我家老爺交代,讓我片刻不能離了小姐!」
主事的婆子好笑:「人家夫妻洞房,你也陪著麼?」
藍藍又羞又急,頓足道:「本來不能答應的!如此毛躁,算什麼?」說歸說,終於還是挪步出了屋子。
其他侍侯的丫頭也紛紛掩門出去,屋內只留兩頂不言不動的紅蓋頭,紅燭高燒,錦被層疊,我不由心有所感:「大公子呀大公子,真對不住了,你的愛婢小菁先入了我手,浣兒雖不能算你的,但她對你有情意,也算我冒領,如今不好意思,我又要對你的嬌妻下嘴了,怪只怪你福薄,你既不在,只有我代勞,天意使然,怨不得我胡吃海喝了!」
想了一想,正妻為大,先到陸小漁跟前,將她紅蓋頭掀開。紅蓋頭一去,低垂著一張亦紅亦白的粉面,我不知之前大公子如何稱呼她,便啟用了現成的新稱,道:「娘子!」
「筠哥兒,」新娘緩緩擡起一張嫵媚的瓜子臉,長長的眼睫忽閃:「先別忙叫『娘子』,我要跟你約法三章!」
我唬了一跳:「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陸小漁的神情含羞帶惱:「大家這都為哄老太君高興,當不得真!沒有父命,我還不能算是你賈家的人!」
我一愣:「那磕頭拜天地算什麼?你穿這身衣裳、來這洞房……」
「那是做給老太君看的!」陸小漁面色一紅:「做小輩的,再怎麼委屈自己,孝順老人,那也是應當,所以她們來勸我,我也只能答應。但你也得替我想想,我午覺方醒,就給人弄到這邊,一生嫁一回,什麼準備都沒有,就這樣進你賈家的門麼?」
「你……你想怎麼樣?」
「所以要跟你約法三章,第一,你將我當客人,不許……不許對人家無禮。」
「咦?」
「第二,我要乘花轎,吹吹打打,光明正大進你賈家的門,要朝公婆磕頭見禮。」
「那就是在西邊府上重辦婚事?」
「對,世上那有婚事避開公婆的道理?」
看來,她也知道兩頭賈府的宿怨,特意提起,是不願只躲在東府,做個見不得公婆的兒媳。
「嗯,還有呢?」
「第三麼……筠哥兒,你忘了答應過的那件事了麼?」
糟糕,這才最頭痛!動不動叫我記起「前事」,我往後還怎麼活?更可怖的是,她臉上神情怎地那般古怪?實在叫人猜不透呀。
「就知道你會忘,反正也不急,你慢慢想罷!」陸小漁抿嘴一笑,道:「浣兒妹子頭都垂酸了,還不快去掀了紅蓋頭?」
那邊浣兒聞言一動,頭上紅布直晃。
我心下癢癢,走過去,猛一掀,浣兒如給人解了穴道,羞望了我一眼,隨即轉頭向陸小漁怯怯地叫了聲:「姐姐!」
陸小漁點頭道:「浣兒妹子,咱們往後是一家人了!」
浣兒又喜又羞,面色猶帶不安:「我方才被表姐數落了一通,姐姐,你真不怪我麼?」
陸小漁道:「怪你什麼?」
浣兒咬了咬唇,道:「你……你的大喜日子,卻多了我添亂。」
「不對!」陸小漁唇角微笑:「你沒聽我跟筠哥兒說話麼?今兒我是客,你才是正主兒!」說著,竟盈盈起身,走向小圓桌邊,捋了捋寬大的吉服袖口,執壺倒了兩杯酒,以小盤端了過來。
「請兩位新人喝交杯酒!」
那明亮的慧目朝我望來,她藉機重申己志的意思,再明顯不過。難道她真打算洞房為客,做個守身的新娘?
浣兒哪裡敢受,登時慌了,小臉通紅,忙也起身,至桌旁倒了一杯,舉杯結結巴巴道:「姐姐與……與公子喝交杯,我……我只能算作陪。」
想不到浣兒也有她的心慧處,這樣一來,她算是擺脫困境了。我望了兩人一眼,笑道:「怎麼,沒人肯與我交杯?娘子,約法三章裡可沒這一條呀。」
陸小漁一手托盤,一手至浣兒手中搶過酒杯,一口喝了,杯口一照,道:「好了,該喝的酒我喝完了,只剩了你們倆!」
陸小漁看著雖溫婉和順,其意甚堅,不管事情原本的是非曲直,她始終不慌不忙,巋然不動,神情從容自若,無理也顯得有理,最終我與浣兒都拗她不過,在她目視下,把交杯酒喝了。
飲完之後,我與浣兒像上了她的賊船,再也下不來了。走了這一步,剩下的一步步,更是理所當然。
她從新娘的身份,儼然變成居中牽線、執事侍侯的第三人。浣兒平日甚是敬服她,扭捏無奈中,只得依從,而我雖覺好笑,卻又拗不過她,不過,也暗暗存了一份心思,要瞧她究竟如何擺佈——外邊守著滿屋子聽喚侍侯的僕婦婆子,她指定不能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出屋。而新娘子洞房之夜若是奪門而出,傳出去,定成奇聞。可是,她若留在房中,三人之局,如何了結?莫非我與浣兒暢諧花燭,她在一旁聽床觀景?
直到要服侍新人登榻,寬衣就寢時,她才意會於此,陡然羞縮:「哎喲,完了,我今晚睡哪?」
這是她多事而生出的難題,我與浣兒自然不會替她出主意。實際上,我早等著看她笑話呢。
她咬牙半日,隨著忖思,腳下緩移,那襯飾著華麗霞披的寬大吉服,罩著她嬌俏的身子,前胸嬌聳,後腰纖盈。乍望去,她上半身動也不動,自然而然保持著一種舒挺的女子姿態,裙下款款而行,如龍舟破浪,香裙過處,滿室為她頓生風色。我心中讚歎,這才是閨閣淑女,連行步的姿態都如斯之美,我見過的諸女,師姐、趙燕非修道練武,固然走不出這步姿,小菁、小荃等同是深居高門大院,沒這樣的氣韻,棋娘、賈妃雖美,卻少了那處子之態。
她到了花燭前,以簽挑焰,燭光跳動,映照其面,容色有若年明珠生光,霜雪欺目。
我暗生了一個呆念:賈大公子怎配得上她?她怎會喜歡賈大公子的?隨即又是心喜:如斯美人,如今竟然歸我了!
我這裡胡思癡想,她剔高燭焰,走了回來,似乎有了主意,揚頭道:「罷了,浣兒妹子,你過來!」
浣兒乖乖過去,藉著撒嬌,勾頭依入她懷中:「姐姐,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浣兒為難死了!」
陸小漁不言不答,替浣兒拿下頭上鳳冠,將浣兒身子推轉,又解她霞披,除其外裳,浣兒禁不住癢,咯咯嬌笑,羞瞄了我一眼,扭身躲閃。
「癡丫頭,怕什麼羞,你身上哪處不屬於相公?遲早要盡他貪看,這時躲個什麼?」
我暗下好笑,她哪知道,我與浣兒早暗渡陳倉,春風數度了,何止貪看身子這麼簡單?
她下手也真狠,不一會,竟將浣兒上身扒了個精光!
「啊!」
浣兒猝不及防,急掩胸前小乳,露著瘦小的肩身,像個受驚的小兔,吃驚地望著陸小漁。
「去,拿被兒蓋著身子!」
她喘著氣,神情似厲似怒,喉音低沈,有種不可抗拒的威嚴。浣兒不知其意,畏怯地撩帳上榻,瑟瑟地躲入被中。
我一錯眼,不知她們兩人間發生了什麼,一時還以為浣兒惹惱了她,卻見她胸前起伏,暈生雙頰,眼波水亮水亮,又不像在發怒。
見我疑惑詢望,陸小漁烏亮的眼珠回盯我一眼,也不說話,自落鳳冠於旁,我上前欲助她解霞披,她玉手輕按在我手背,擡首啞聲道:「筠哥兒,今夜你先別碰我,好麼?」
我笑她迂腐:「何苦呢,進了洞房,旁人會信你是完壁潔身麼?」
她道:「旁人說啥,我都不管,我要以處子之身坐轎嫁你,這是我向來的心願,別人都可騙,只有自己騙不了,你能成全麼?」
我為她的堅持感動,柔聲道:「我依你。」
陸小漁將手鬆開,由我幫她解去了覆肩的霞披及寬沈累贅的吉服。她身著月白中衣,襯著她水靈靈的垂睫大眼,如雲烏髮,格外透著精神與嬌媚。
她柔順地貼入我懷中,眼卻向後邊榻上望去,低聲羞道:「筠哥兒,我想……想看你與她如何行房……」
我聽了慾火大動,以手輕擡她下頜:「你真想看?」
她點了點頭,仰擡的眼波像陷入絕望的孤境,不可名狀的情慾在無聲燃燒,卻毫不掩飾,大膽地迎著我的直視,這真是個奇女子,一時竟讓我有自慚形穢之感,非得情真無偽,豪放不拘,方能與她相配。
「好!」
我抄起她腿彎,將她高高抱起,只覺她身子飽沈,肌膚隔著薄衣觸接,格外膩滑水嫩,渾身毫無骨感,便似一尾魚兒一般。
我靴也未去,逕舉步登榻,將她朝浣兒裡側放落。
她嬌沈沈地從我臂彎滑落,先以一臂支撐榻面,隨即歪坐榻上,將繡鞋從足尖摘下,遞給我丟擲榻下,又解下外裙,將紅裙搭於榻側,紅裙一去,她上著月白中衣,下著粉紅紗褲,身姿更見玲瓏有致。
她做這些舉動時,並未看我,不緊不慢的,旁若無人,姿態那麼柔美宜人,直到收拾停當,轉首望我時,才忽覺害羞,縮身挪至榻角,似乎為我騰開地界,她兩腿曲起,將下頜抵至膝蓋處,睜著又羞又緊張的大眼,定定的看我。
我心下一陣陣激動,吐出的呼吸都是滾燙的,眼兒緊盯著她,除靴去袍,待解去下體遮蓋時,見她兀自亮眼灼望,微一遲疑,便將布兜除下,塵根血氣沈沈,自覺比往日累贅而巨。
陸小漁驚噫了一聲,擡臂遮目,像遮擋刺目的光亮,羞嗔道:「你好放肆!」
「此時不放肆,更待何時?」
有她在一旁注目觀看,我像頑皮胡鬧似的,變得格外放肆大膽,說話間,傾身揭開錦被,浣兒捲曲的小巧身子全露了出來。
{:4_375:}這麼好的帖
不推對不起自己阿
我最愛了{:4_375:}
這麼好的帖
不推對不起自己阿
我最愛了
感謝大大的分享
好帖就要回覆支持
太棒了
路過看看。。。推一下。。。
我一天不上就不舒服
路過看看。。。推一下。。。
分享快樂
路過看看。。。推一下。。。
我覺得是註冊對了
路過看看。。。推一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好帖就要回覆支持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