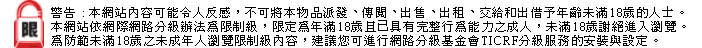我和日本小護士
事情還得從辦奧運的那年夏天說起。至今我都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七月一號,星期二。本來很平常的一天,我簽了兩單生意,陪客戶吃過晚飯,回家洗洗便睡了。後來就出事了,我突然小腹劇痛,難以忍受,只好打110叫來救護車,便被就近送到了中日友好醫院。擡進急診室的時候,我的意識還是清醒的。值班護士小野純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倒不是因為她的日本名字,在這所醫院裡總是有交流實習的日本醫生和護士。讓我吃驚的,是她的相貌和神態,是那麼刻骨銘心的似曾相識,我努力搜索著記憶,以致疼痛都似乎減輕了釵h。就這樣,我躺在了手術台上。
我的病很簡單,急性闌尾炎。主刀的值班醫生也是日本人,胸牌上寫的是佐籐一郎。當第一刀切下來時,劇痛使我禁不住一聲慘叫,睜開眼,是小野護士輕篾的目光。在這一瞬間,我終於想起來了,為什麼這個小護士這樣面熟。記憶象開了閘的洪水。我咬緊牙關,沒有再坐@聲。終於縫上了最後一針,小野護士突然失聲喊道:「天哪,我忘記叫麻醉師了!」「八嘎!」緊接著的,是一聲怒吼和兩記耳光,小護士的雙頰頓時腫了起來。「醫生,請不要怪罪小野護士,是我堅持不要麻醉的。」我操著不熟練的日語替小護士開脫著,「我們家族的人,外科手術從來不要麻醉。」
在高級病房裡,我躺了五天。我沒有再見到小野純子,聽換藥的護士說,佐籐醫生本來要吊銷她的執照,幸虧我講了好話,只是讓她做了深刻的反省。在這日日夜夜裡,初戀女友和小野護士不斷地交替浮現在我的眼前。二十年前,我考上了城西的一所地方大學,並且很快就交上了女朋友。那是一個美麗清純的姑娘,我很愛她,可是她對我並不滿意。那年月,時髦彈吉他,跳交誼舞,談論薩特和弗洛伊德。作為體育特招生,我本來就不喜歡讀書,對小資的那一套更是反感。
終於,我的女朋友移情中文系的一個滿口「存在與虛無」的才子。我決定用男人的方式解決問題,結果因打架斗毆進了派出所。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女朋友,不,確切地說是那個才子的女朋友輕篾的目光。後來,中越在南沙打了一仗。再後來,我沒有參加畢業分配,參軍去了赤瓜礁。再再後來,我退伍了,領著幾個戰友開了一家汽車配件商店。
牆上的掛鍾告訴我,午夜過去了,七月七號已經來臨,我逼迫著自己揮去腦海中初戀女友和小野護士重疊的倩影,沈沈地睡去了。在夢中,我又一次回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太行山的十字嶺。大地在顫抖,天空仿佛在燃燒,日本鬼子漫山遍野地湧來。我精疲力盡,背靠著一節樹樁,雙手緊握著的大刀已經卷了刃。我把刀斜向右下,刀背向敵。一個鬼子突刺過來,我奮力掄刀斜向左上,「當」地一聲,鬼子的步槍被磕飛了。不等對手緩過神,我一刀劈下去,砍翻了那鬼子。
這時,又一個鬼子撲了上來,我來不及拔刀,腋窩已經被刺中。八路軍寧死不當俘虜!我用盡最後的力氣,抱住鬼子滾下了懸崖。
每年的七月七號,我都在重複著這一噩夢,在夢裡,我總是分不清到底是我自己還是爺爺。每一次,我又都在一身冷汗中驚醒,這一次也不例外。我睜開眼,卻發現房間的燈是亮的,小野護士站在床前。
「對不起,剛才您喊叫得很厲害,是不是傷口在痛?」
「傷口不痛,心口痛,還不是你們日本人弄的。」我沒有給日本小護士好臉色。小護士也當然無法正確理解。
「是這樣的,那天麻醉的事真是給您添麻煩了。我一直想當面致歉,可又不知該如何才能深刻地表達。」
「唉,讓你們日本人道歉可真難,那麼你現在知道該如何表達了?」
「是的,請您一定給我這個機會,拜托了。」
小野護士端出一個盛滿溫水的盆,擰了毛巾,解開我的上衣,輕輕擦拭起來。
由於出過一身冷汗,我的身上黏滋滋的,這樣的擦洗,使我感到很舒服。我閉上眼睛享受著,思緒又回到一九四二年的十字嶺。我的爺爺跳崖後並沒有摔死,幾天後,一個村姑,把他從死人堆裡背了回去。命保住了,但一條腿已經摔爛壞掉,村裡的老郎中用木工鋸給他截了肢。爺爺痛得幾乎昏過去,但他就是不喊一聲。
村裡的人都說,八路真是了不起。後來,那個村姑做了我的奶奶。
小野護士繼續工作著。我的睡褲被解開,溫熱的濕毛巾在我的下身遊走,慢慢移向大腿內側和腹股溝。我感到全身發軟,一處發硬,但我的意志並沒有發軟。
那一次十字嶺突圍,八路軍總部死傷慘重。機關、後勤、學校,數千人陷入重圍,前有懸崖絕壁,後有殘暴的倭寇。為了不落入敵手,有槍的留下,沒槍的跳崖。
深谷裡回響著物體墜落和撞擊的聲響,有儒雅的學者,也有稚嫩的少女。面對敵寇,他們選擇了尊嚴。溪流被染成了紅色,山谷裡鋪滿人和騾馬的屍體。我猛地坐起身,憤怒地命令日本女人:「解開我的內褲,那裡也要清洗!」
小護士渾身顫抖了一下,沒有說話,溫順地垂下頭,一雙小手隔著薄薄的內褲在我的襠部揉捏。我全身燥熱,難以抵擋。在小護士的巧手搓揉下,陰莖已經脹得巨大。小野護士輕輕拉下我的內褲,挺立的肉棒立即跳將出來。小護士羞澀地握著巨棒,溫柔而熟練地揉搓起來。這些年我雖然沒有結婚,身邊並不缺少女人,但我從未想到過,手淫的感覺竟能如此奇妙。日本人真是敬業啊!眼看自己的陰莖愈來愈大,我忍無可忍,一把扣住小護士的下齶,輕輕一捏,小護士張開了嘴,我拉住她往身前一帶,粗壯的陰莖便塞在了日本女人的小嘴裡。
小野護士含住陰莖的上半部份輕輕吸吮著,柔軟的舌頭熟練地舔著腫脹的龜頭。「好舒服啊。」我陶醉在陰莖上傳來的連綿不斷的溫熱穌癢中,擡起頭來,我看見昏黃的牆上,一個婀娜的身影撅著屁股,俯在男人的胯間,充滿韻律地上下簞妗菕C日本女人就是不一樣啊!不知為何,小野護士的每一個動作都讓我興奮無比。她一面揉搓著我腫脹的陰囊,一面套弄著我陰莖的根部,嘴裡的東西愈來愈大,也愈來愈硬。我躺下身,讓粗壯的陰莖更加深入日本女人的咽喉,坦然地享受著溫柔細致的日式服務。
小護士大張著嘴,將肉棒深深地含住,賣力地加速套動著。我的陰莖濕漉漉的,胸中的欲火越燒越旺,我開始大聲喘息。終於,經受不起這樣的刺激,我不由自主地坐起來,按住她上下運動著的頭,粗大的陰莖更加深深地插入口腔,直抵咽喉。她劇烈地幹嘔起來,但我完全陶醉在抽插溫濕的口腔帶來的快感,哪裡還顧得上日本女人的感受,只管按著她的頭繼續猛烈抽動。快感一浪高過一浪。
牆上的倩影中,俏麗的護士帽被一次次按下,又一次次拔起,越來越急,越來越快。突然,一切都停頓下來。我緊抱著小護士的頭,死死抵在胯下,一股濃濃的精液,直噴進她的口腔深處。
小護士喘息著,捧著雙手,滿嘴的精液緩緩流淌下來。
「伺候的不好,請多多原諒。我可以回值班室了嗎?」清理了我的下體和她自己的顏面,小野護士怯怯地問到。
「騷貨,你以為這就算完了?脫掉褲子,趴在床邊,撅起屁股等著!」
待我喝完一杯水,日本女人已經按照吩咐準備好了,她雙手撐住床沿,短裙和內褲褪到腳下,白皙豐滿的屁股高高撅起,粉嫩的陰唇間濕漉漉地淌著春水。
看在眼裡,我的陰莖又堅硬得如同鐵棒。我雙手把住小護士的腰,頂在濕潤的兩片陰唇之間,晃了一晃,“啵茲”一聲,整根沒入。「啊」地一聲,小護士渾身顫抖,巨大的陰莖強行插入帶來的痛苦,讓她撕心裂肺。她咬緊牙關,眼�水奪眶而出。我瘋狂地連續抽插了幾下,日本女人緊密的陰道讓我無比快樂,從未有過的暢快淋漓傳遍全身。我深吸一口氣,停了下來,抽出半根陰莖,一面體會著被女人緊緊包裹的感覺,一面給可憐的日本女人一點喘息和適應的時間。
日本女人狗一般趴著。望著白嫩的屁股,豐腴的大腿,和白色的透明絲襪,我無比興奮,慢慢地恢複了抽動。隨著一次次的探索和包容,陌生的肉體漸漸相互熟悉。痛楚在消失,留下的只有全新的刺激和無比的歡愉。小護士的陰道越來越濕潤,日本女人的適應性真是舉世無雙啊!她整個上身軟軟的癱下來,隨著我的抽插晃動著,一股股淫水順著白嫩的大腿流淌下來。然而這只是開始,隨著我瘋狂的抽插,一陣陣的熱浪滾滾襲去,把她送上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小護士徹底瘋狂了,她翹起腳尖,半張著嘴,驅動雪白的屁股,奮力迎接中國男人的撞擊。
伴隨著肉體撞擊和摩擦的「啪啪」聲和「啵滋」聲,我愈戰愈勇。終於,中日兩國人民實現了共榮。一股股精液深深地射入日本女人的陰戶,小護士緊閉雙眼,兩頰潮紅,喘息著,顫抖著。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小野護士給我清理幹淨,穿好衣服,然後把她自己也清理整潔,依偎在我的胯間,輕輕撫摸著。
「您真勇敢,又那麼強壯,您一定曾經是軍人。」
「是的,我,我爸爸,還有我爺爺,都當過兵,但只有我爺爺打過仗,和你們日本人。」
「啊,竟然是這樣的!戰爭期間給貴國添麻煩了,真是不好意思。」小護士慢慢地弄到了我的襠部。「我的祖父也曾應征來過貴國,時間很短,他在板垣輜重隊,在一個叫平型關的地方全體玉碎了,他被炸斷了腿,躺在地上裝死逃過去的。」
「是嗎?他怎麼不切腹?」
「切過的,戰敗的時候,可是刀尖剛剛劃開皮膚,他就嚇得昏過去了。就這樣,祖父活到田中時代。」
「這也沒什麼。那個東條英機,也是嚇得握不住手槍。」我不願多談鬼子的那點破事兒,因為我的陰莖,又開始有了起色。「純子,你有過幾個男人?」
「啊,這個,當然是只有一個未婚夫。」
「是佐籐醫生吧?」
「嗯。」
幻想著嚴肅的佐籐醫生此時也陷N在值班室,也鹿H時都可能推開門來查房,我又興奮起來。我把小護士拉到身上,一面親吻著,一面撫摸著她裹著薄薄的白色絲襪的大腿。
「告訴我,我和佐籐,誰厲害?」
「嗯,這個,日本男人很辛苦的,那方面自然差一些。不過,佐籐很關照我的,他買了好幾根震蕩棍。」
「呸,日本男人真他媽的下作。」我繼續撫摸著小護士的大腿,另一只手解開誘人的護士制服,開始用力地揉搓她的乳房。「要是讓你選擇,你是要我還是佐籐?」
「這,這怎麼好意思講。」
「你們日本人還有不好意思的時候?講!」
日本女人最終也沒有講,她只是直起身,熟練地褪下我的褲子,小心地跨坐上來,扶著我的肉棒,將龜頭對準自己的陰戶,慢慢地套坐下去。一陣顫抖,巨大的陰莖已經深入體內,強烈的刺激立即傳遍全身,小護士不由得一聲呻吟。我一把握住她的雙乳,姿意地揉捏著。上下同時產生的強烈刺激,把女人的羞恥心拋到九霄雲外。小護士微睜著眼,緊閉著嘴,陶醉在瘋狂的肉欲之中。雪白的牆壁上,美麗的倩影前傾在男人的身上歡快地上下跳動,無休無止。日本女人的身體越來越燙,也越來越傾斜,她的臉幾乎已經埋在我寬闊的胸懷裡。從未體會過這樣自由主動的交媾,小護士不斷地扭動著屁股,體會著下體傳來的快感和刺激,完全迷失在肉欲的驚濤駭浪之中。我一邊老練地撫弄著雪白的乳房,一邊享受著肉棒在緊密的陰戶裡進進出出的快感。日本女人努力著,很快就進入了瘋狂的境界。隨著一聲忘乎所以的大叫,濕潤的陰道一陣痙攣,緊緊地夾住我的巨棒,小護士的整個上身軟軟地癱塌下來。
對於我,這還不是結束。我翻過身,把小護士壓在胯下,分開她的雙腿,跪在其間。日本女人的雙腿間柔軟光潔,嫩紅色的蜜唇微微顫動。我粗壯堅挺的陰莖熟練地抵住女人的桃源。深深一次呼吸,我俯身抱緊女人光滑的肩背,結實的臀部堅決地向前頂去。她知道該來的就要來了,順從地擡起屁股,長籲了一口氣,讓我的陰莖以最佳的角度侵入,不,是進入。我把舌頭伸到她的嘴裡吸吮著。小護士飄飄然然地眩暈起來,她緊抱著我寬厚的臂膀,隔著薄薄的肉色絲襪,她的雙腿死死纏繞著我的腰身,隨著我的節奏努力迎合著。
長夜即將過去,東方已現出曙光。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我的爺爺,燕京大學的高才生,憤然投筆從戎。而七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卻在這所謂的友好醫院的病房裡與日本女人和親。我開始毫無保留地最後衝刺。在這間密不透風的病房裡,人世間的其它一切都不再存在。溫暖潮濕的空氣中只回蕩著男人粗重的喘息,女人嬌媚的呻吟,軟床不堪重負的吱吱嘎嘎,和濕漉漉的肉體相互撞擊發出的「啪啪」的聲響。終於,胯下的女人又是一陣痙攣,一股清泉湧出她的陰戶。我奮力拼搏著,越來越快,越來越猛。隨著最深的一次插入,一股滾燙的精液直射入女人的身體。我繼續抽動著,伴隨著一股股精液的狂噴亂射,中日關系終於實現了正常化。
等我從衛生間裡出來,小野護士已經把她自己和床鋪都收拾整齊。年輕的姑娘縮在床腳,面帶憂鬱,楚楚動人,我心生愛憐,摟住姑娘柔弱的雙肩。
「純子,嫁給我吧,我會一直讓你快樂的。」
「啊?怎麼會是這樣?我和佐籐有婚約的。」
「婚約是什麼?婚約就是用來撕毀的。」我一只手托起小護士的下巴,吻住她的嘴,另一只手又不安分地探進姑娘的內褲,按在濕漉漉的陰戶上揉搓起來。
「你看,這塊地方是屬於我的。」
「不,佐籐認為是屬於他的。」
「胡說,這塊地方是屬於我們中國的。」
「可是,它現在確實是屬於日本的。」
「中國的。」
「日本的。」
「好了,純子,爭吵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一把扯下小護士的內褲,分開的雙腿,粗壯的陰莖再一次狠狠地頂了進去。「讓我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吧。」
一年以後,我的店裡多了一個溫良謙恭的小老板娘,每天早上站在門口,向第一批光顧的客人鞠躬致謝。對於她的來曆,我守口如瓶,未吐一字,大家只知道她是日本人,曾經做過護士。。